“一个女人”
读完了安妮·埃尔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多久没有这样既痛且快地、泪流满面地读完这样一本书,“一个女人的故事”,我不断地想到我的妈妈、我的奶奶,以及我自己。中文翻译的书名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法语的原书名 Une Femme,在我仅剩的一点法语知识里,我的直觉译文是“一个女人”,法语词典告诉我:femme,女人,妇女,成年女子,妻子,已婚妇女。在代译后记中,(可能是)译者也从未提到这样翻译的缘由,也许“xxxxxxx的故事”这样的表述会更有吸引力,会更有“力度”,可读完这样一本书,我反抗这样的译名,“一个女人”就够了,无需将“女人”作为“故事”的定语来修饰,因为没有故事,全是现实。
在这样完全诚实、赤裸的文字面前,我无所适从,我无处遁形,我的虚伪、掩饰、伪善被剥离。
在书的开头安妮·埃尔诺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声称矛盾是不可构想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实际上,在一个生命体的痛苦中,矛盾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的,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矛盾都存在。
在她母亲(即书名中的“一个女人”)的青年时代,我幻想我的妈妈、我的奶奶,她们富有活力的、但远离我的时代,甚至是没有我的时代是怎样的,一次和家人去小巷里吃某家苍蝇馆子,途径的一条老街——距离奶奶从小长大甚至到现在还居住于此的祖宅不过一公里,她挽着我的手和我说,住在这里的一个年轻男子曾在她知青生涯结束返乡后专程提着自家包的馄饨到她的家里来拜会,她曾经使用过的一个黑色的电话本里还记录过他的电话号码,只是现在遗失了。
我试图翻找我与奶奶重要的聊天记录,在六月,我还记得是我翻阅了一本叫《秋园》的书,和奶奶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奶奶”书写自身与自己母亲的一生,当时我又动力满满,想要也写点什么。
于是我在微信中问:“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啊?”
她回复我:“你和谁说话?”
(我常常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她在微信上聊天,她常批评我作为一名拥有本科学位的“知识分子”不使用任何标点符号,我的应对方式就是发擦汗无语的表情来敷衍回应。)
“你。”
“我的曾祖父祖母。”
“我爸爸一生没做什么工作,后来就同医院送药,搬运公司,我妈妈是妇幼保健所。”
这句话之后,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提问了,便搁置了。
我时常想为她写些什么,又怕冒犯到她,她总是很敏感,很细致,特别是对我的一切,像女生会细细剖析自己迷恋的男生在网络上的一切踪迹,而她只拥有我的朋友圈。
上周她突然给我发来一段长达36秒的语音,她说:我认为我自己的文化水平还是低了,像你的朋友圈里的东西,除开照片,那些东西我都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问她怎么回事,突然说这个。她回我:你不是发了朋友圈什么随机波动书做好了,两年之约,我就不懂呀,我只看得懂你的照片。我就说我的文化还是差了些,基础还是可以。我哄她,就是出了本书,你都读得懂,你还会说俄语呢(我不会)。她又发来长长的语音,开始谦虚,说自己不会俄语,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只会“斯巴si吧”,谢谢,这就是俄语。
安妮·埃尔诺在另一本名为《写作是一把刀》的序言中写:
当我在二十多岁开始写作时,我认为文学的目的是改变现实的样貌,剥离其物质层面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人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得到升华,它们是不能进入文学的。……地下堕胎的现实,我负责家务、照顾两个孩子和从事一份教师工作的婚姻生活的现实,学识使我与之疏远的父亲的突然死亡的现实。我发觉,写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通过我所经历的,或者我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察到的,把现实揭露出来。第一人称,“我”,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工具出现,它能够锻造记忆,捕捉和展现我们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东西。这个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除了理解和分享之外,没有其他的顾虑。
我所写的书都是这种愿望的结果——把个体性和私密性转化为一种可感知的和可理解的实体,可以进入他人的意识。这些书以不同的形式潜入身体、爱的激情、社会的羞耻、疾病、亲人的死亡这些共同经验中。与此同时,它们寻求改变社会和文化中的等级差异,质疑男性目光对世界的统治。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有助于实现我自己对文学的期许:带来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
我也曾怀疑过书写自我的一切,我的自我意识是不是过分强烈,我毫不顾忌地自我剖析,意义何在?我也认为这是“低于文学”的。我现在知道,写作对我来说也只能是这样:我是我的工具,我是文字的笔,words are my matter。友人在“鼓励”我写作时,对我说:你责任重大。我想,或许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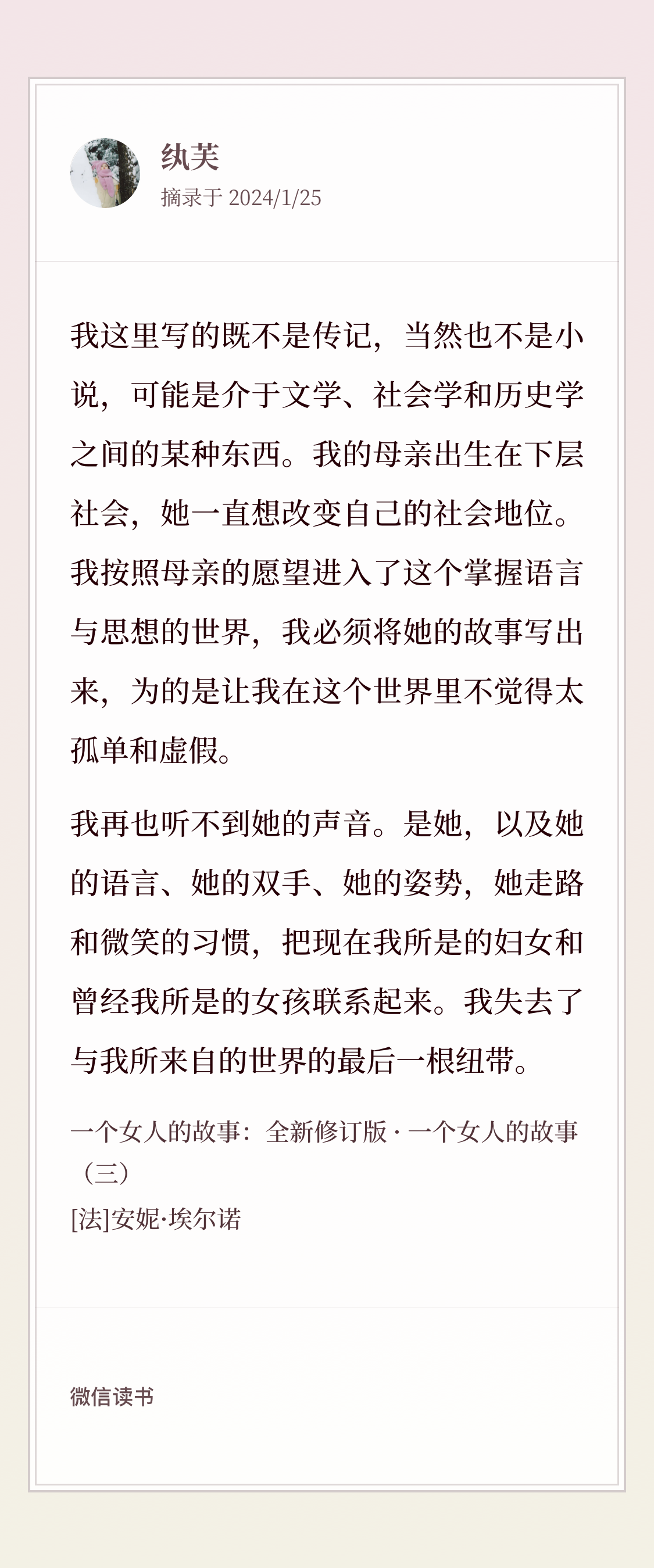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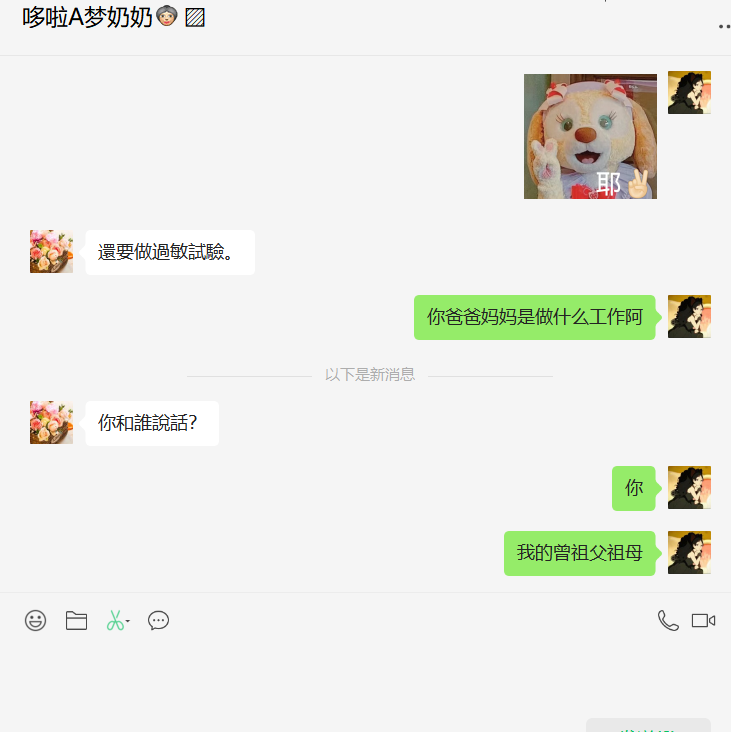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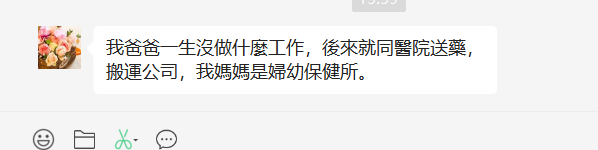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