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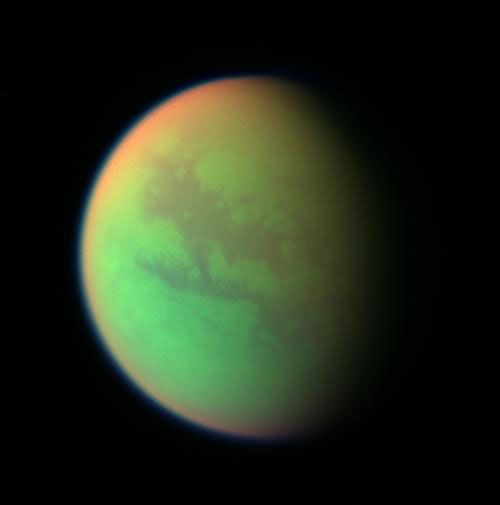
Raymond
24
一個平靜的24歲結束了。
責任
我對我所做、所說,乃至所遭受的都負有責任,意味著我可以回應我自出生起累積且承載的所有經驗。
山
「哪裡人」這個問題的弔詭之處在於它預設的回答是「來自哪裡」,而不是「往哪裡去」。
黑暗
黑暗不意味著未知,而是一種能讓已知之物進一步呈現的媒介。
邊境
我在尋找的同時,也是在記憶;我在記憶的同時,也是在遺忘,畢竟記憶永遠伴隨著遺忘。

在海上
12月22日早上9點10分,我登上尼什快運公司的巴士,由尼什前往貝爾格勒。這一段250公里的路程需要3小時。巴士駛出那個看起來如同城鄉結合部的塞爾維亞第三大城市,蒼白的陽光與尚未消散的霧氣加上路邊栽種的葉子掉光的樹,毫無看點的窗外景象孵化著車廂內乘客的睡意——所有人都無意識地把命運交給那個清醒的戴著墨鏡的司機。
流亡
我永不返鄉,我永不投降。——納博科夫
回歸
我站在伊斯坦堡獨立大街的盡頭,對恐襲的惶恐已經消散,或者已經無畏。因為我就站在那兒,在共和國紀念碑下,與所有人,那些早已摘掉口罩的多樣化的個體一道,用參差多態的真實重構著仍在經歷陣痛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