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活人祭和社会暴力的探究:读略萨的《利图马在安地斯山》
野兽按:巴尔加斯·略萨因“他对权力结构描绘,以及他那反抗、起义、失败的犀利印像”获颁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2月3日,被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依Real Decreto 134/2011号令,成为第一代巴尔加斯·尤萨侯爵(Marquesado de Vargas Llosa)。他近日曾于 El Pais发表题为“回到中世纪”的文章,称“病毒来自中国”,并且由于该流行病,人们在恐惧瘟疫的情况下生活,这表明社会重返中世纪。
他还写道,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的独裁政治制度,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这凸显了一个事实,即在疫情爆发之初试图吹哨的医生“被沉默”了,并且拖延了本可以用于研发疫苗的时间。据悉,截至2020年3月15日,秘鲁已确诊71例新冠肺炎病例。

傅正明|活人祭和社会暴力的探究:读略萨的《利图马在安地斯山》
在《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中,略萨对秘鲁内战中的统治者和革命者两种权力结构,均有精彩描绘。革命者杀红了眼睛。平叛的秘鲁国民卫队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施暴,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控制局势的能力。
《旧约》中的恶人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之后,建了一座城。他的祭品并不被上帝悦纳。威廉.布莱克在<亚伯的鬼魂>中写道:“该隐之城是用人血建造的, 不是牛羊的血。”
本届诺奖得主、秘鲁作家巴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小说《利图马在安地斯山》(Lituma En los Andes)的扉页题词,就是布莱克这句话。
略萨有句名言说:“作家是他们自身的魔鬼的驱魔者。”以佛家的观点来看,任何有心向善的人都要驱除内魔。青年略萨一度加入秘鲁共产党,六〇年代同情毛派革命,后来日渐转向右翼,投身民主政治。不以政治阵营的眼光来看,就不难发现,略萨的转变,正是他不断驱除内魔的过程和结果。
《利图马在安地斯山》出版于略萨的思想和艺术均已成熟的1993年,是他最重要作品之一。小说情节设置在八〇年代发起的秘鲁革命和内战时期,主人公利图马是政府军的军警,他和他的副手卡列诺被派遣到一个偏远的高地山镇,以寻找在筑路营失踪的三个人:一个哑巴,一个商人,还有一个是筑路工头。利图马开始接触他原本陌生的高地印第安人和印加文明。在茫然寻觅中,为了解闷,卡列诺每天夜里给利图马讲述他与一个妓女的罗曼史,他也在寻找这个得而复失的恋人,由此构成小说的一条缓冲紧张气氛的情节副线。
另一条更重要的副线是逼近山镇的“光辉道路”游击队,即从秘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毛派分子的造反活动。在复杂的结构中,含有侦探小说、政治讽喻和爱情故事色彩的几条情节线索,平行交叉发展,最后融汇在一起。与之天人感应的自然景观,是小说开篇的黑云雷暴,笼罩头上的死气沉沉的蛊毒瘴气,以及后来的地震山崩。这一高地的黑白艺术画廊,实际上是那一恐怖时期整个秘鲁的缩图。
在革命与平叛的祭坛上
有阅历的中国读者读《利图马在安第斯山》的原文或英译,有时也许难免产生这样的感觉:仿佛在读一部中国小说的外文译本。略萨笔下的那些革命场面,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太熟悉了:山地那些男男女女的“革命者”,甚至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扛着机关枪、或手持刀枪棍棒,三、四个人一组,依照黑名单,半夜三更直闯“阶级敌人”的家门,上至市长,下至无辜的农场工人,妇女环保人士,一概从睡床上拖出来带走。……公审大会开始了,那些五花八门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在卡夫卡式的“审判”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被“革命群众”鞭笞,被枪毙,被棍棒、石头活活打死。酷刑拷问、强奸妇女成了家常便饭。从外国来游客也被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死于非命。
瑞典学院把诺奖颁发给略萨,“由于他对权力结构的描绘及其个人的抵抗、反叛和招致挫败的鲜明形象”。在《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中,略萨对秘鲁内战中的统治者和革命者两种权力结构,均有精彩的描绘。革命者杀红了眼睛。平叛的秘鲁国民卫队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施暴,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控制局势的能力。
后来,根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在多年内战中,政府军和游击队均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将近七万死难者,大多数是革命与平叛祭坛上的无辜牺牲品。
神话和祭祀山鬼的活人祭
在恐怖的屠杀风暴中,小说主人公利图马预感到难以从山镇活着出去,他疑惑地问道:“许多劳工都接受了现代生活方式,至少念过小学,见过城市,听过收音机,看过电影,穿着打扮跟文明人一样,可是,可他们的行为怎么像赤裸的吃人肉的野蛮人一样,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 ” 在略萨看来,把秘鲁毛派仅仅视为对中国的革命暴力的一种效法,那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是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挖掘人性恶的內魔。
利图马发现,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今天的旅游胜地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城堡的墙石,就是那些山地人的祖先搬上山头的。在小说中,从这一城堡的建造到流产的筑路工程,都是以人血作水泥材料。
小说中一位前来考察的丹麦人类学家,比一般秘鲁人更了解印加文明宰杀活人祭祀神灵的历史,他使得利图马想起阿兹特克人的祭司站在金字塔顶部举行活人祭,撕裂牺牲品的胸口的惨状。甚至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殖民战争,也没有如此残暴。在今天的高地,关于山鬼吸人血吃人肉的神话仍然口耳相传。依照民俗,在建庙筑路之前,均要以活人祭和人肉筵席来安抚山鬼。高地仍有一个巫婆,很可能还在操办古老的祭礼――与古希腊的纵酒饕餮、歌舞狂欢的酒神节期间相类似的活人祭。
由此可见,“光辉道路”屠杀“阶级敌人”和“肃清”阶级队伍的举措,以及革命者欢庆胜利的盛典,均有其古老的活人祭、净化和狂欢的宗教仪式的渊源。青年略萨学习过的马列主义理论,其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已经成为一种准宗教。小说中的游击队许诺那些参加革命的人:鲜血不会白流,流一份血,就有一份报酬。可是,这种“血酬定律”和乌托邦的许诺,往往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与作者通过主人公的深层探究相呼应的,是难以彻查的那三个失踪者的来龙去脉。他们好像不是游击队绑架的。大致查明的那个哑巴的命运是富于象征意义的:他最初受到游击队的攻击,后来又遭到利图马的一个上司的拷打,最后成了巫婆操办的活人祭的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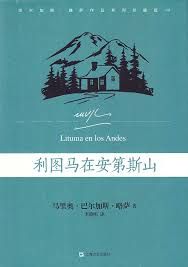
微弱的希望之光
在略萨笔下酷肖现实又扑朔迷离的故事中,在利图马和卡列诺的身上,可以发现一种微弱的希望之光。
尽管利图马隶属于国民卫队,但由于他是有西班牙血统的混血儿,性情温和,态度和善,他成了高地人眼里的外星人。在他身上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但他并不是完美的理想人物。他的探究,并不纯粹出于良知,更多地出于文化猎奇。不滥杀无辜,是他起码的道德操守。当他在比较爱情的狂热与革命狂热时,他告诉卡列诺说:“至少,当你爱得发狂时,除了你自己之外,你不会伤害任何人。”
卡列诺热恋的那个妓女,是他从一个毒枭手里救出来的。在他眼里,她虽然有点偷盗和撒谎的毛病,却富于典型的女性美。他把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寄托在她的身上。他的爱的失落,象征着他的爱国情感的失落。那个巫婆劝慰他说:“是一种爱给你带来不幸,使你受难,你的心每个晚上流血。但至少会帮助你继续活着。”
小说的警策意义,最后通过那个人类学家道出来:“秘鲁正在发生的,并不是埋葬暴力之后的万物复苏。暴力似乎隐藏在某处,突然之间会由于某种原因而重新抬头。”
活人祭与牺牲精神
活人祭蕴含的古老信念在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安全或幸福,必须建立在少数人牺牲生命的基础上。针对少数人的暴力和人权侵犯,就这样合理化了。
从历史上来看,敬神的活人祭在古代社会恶性变异的著例,是宰杀活人为王侯陪葬,这在印加文明中是非常普遍的,在今天的秘鲁已有多处考古发现。此外,处死宗教异端的火刑,也是活人祭的遗风。但活人祭也有良性的发展:首先,是掌权者和祭司力戒屠杀无辜的奴隶,选择罪人作祭品。然后,在有些文明中,活人祭变为象征性的,例如古希腊一种净化仪式中的替罪人,有时并没有被真正处死,只是接受轻度鞭打石击。最后,取代活人祭的是动物祭或动物的血祭。
今天,活人祭虽然在世界上基本绝迹,但变相活人祭仍然见于专制国家维稳的祭坛上,在那里,其合理化的观念仍然是人心不容易驱除的內魔。
像英文词sacrifice 表明的那样,“献祭”与“牺牲”是同一个词。在宗教伦理和哲学中都有所谓“献祭或牺牲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acrifice)。人类既要根绝残酷的被献祭,又可以从原始文明中吸取这样一种有益的精神: 自愿的牺牲――不是血肉生命而是个人利益的牺牲,例如,个人财富或时间的牺牲,义务献血,或死后捐献器官等有利他人或社会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远是人类需要弘扬的高尚品格。这是恶中生出的善。对于那些为了某种高尚目标而甘愿牺牲生命的英雄,我们也应当理解、尊重,不能往他们的遗体上泼犬儒的脏水。
略萨尚未出版的最新作品,即他以爱尔兰诗人和革命英雄罗杰.凯塞门(Roger Casement )为主人公的小说《英雄梦》,就是弘扬这种牺牲精神的。 2009年7月,略萨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表示:在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中献身的凯塞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谴责人的自私,谴责那些除了自我利益之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价值的人。他非常慷慨,一生都围绕着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伟大目标,绝对准备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用于人道组织和文化组织。”
活人祭和社会暴力的根源,及其相关的悖论,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继《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之后的 《英雄梦》, 也许只是略萨继续探究这些问题的一个逗号。
来源:《联合早报》2010年10月29日

美联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在中国批评专制政府
核心提示:秘鲁作家、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家得主巴尔加斯・略萨在上海的发言中批评了专制政府,但国营媒体皆略过了此节,未作报道。
北京——专制政府会腐蚀社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告诉中国学生,而国家媒体上的报道没有提及他的政治意见。
这位秘鲁作家周二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被授予名誉教授时发表了讲话。他没有直接提及中国,而是说在他1969年的小说《大教堂的对话》中想表现的是,“独裁和专制的政府如何腐蚀了整个社会”和“有效地败坏了政治色彩更淡的活动,这些活动又进一步地远离政治,使之更为腐败堕落。“
“不应只把政治留给政客,因为这样的话政治就开始出错了。”作者对西班牙语学生这么说。 “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参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活。正是从参与开始,才能结出最好的果实。”周三的中文媒体只集中报道了略萨的文学意见,以及获得了诺奖之后,他的工作和生活如何被无休止的媒体采访干扰了。中国的媒体都是国家控制的。
巴尔加斯・略萨可能已经不受威权政府的欢迎了,因为去年他表达了对狱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支持。
刘晓波在2009年底被判处11年监禁,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去年年底两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巴尔加斯・略萨称刘为“一名中国战士,在他的国土上赢得了民主的桂冠。”
巴尔加斯・略萨本次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进行为期九天的学术之旅。周四,一个政府智囊的外国文学机构要授予这位作家荣誉研究员的称号。其他得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过去也得到过同样荣誉。
原文:In China, Vargas Llosa criticizes authoritarianism
作者:LOUISE WATT
时间:2011年6月1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贝岭:给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1](Mario Vargas Llosa)的一封信
巴尔加斯·略萨先生:
您好!
从中国媒体上获知,您将於6月12日抵达中国进行文学访问。可以想见,您的中国读者、研读过您作品的中国作家与学者正等待着您的到访。勿庸赘言,中国之行於您、还是於中国人民,都是难得的。
此刻,我是作为国际文学共和国的一位公民给您写信。
您或许记得,2003年11月於墨西哥城召开第六十九届国际笔会年会期间,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我是作为“中国独立笔会”创会人与会,在场的还有南非小说家娜汀·葛蒂玛(Nadine Gordimer)[2],娜汀是一位伟大的英语小说家,也是2000年夏末将我营救出北京监狱的恩人。作为国际笔会前主席,您在那次年会上的长篇演讲既展现了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广阔的画面,也描述了当今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和文学与生俱来的冲突。
余生也晚。同样身为作家,从早年读您的长篇小说《绿房子》起,您在我的文字或精神生涯中重要,二十多年来,我是您小说及散文始终如一的读者。
在我看来,您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西班牙语小说家,也是一位涉入政治的文人。我刚刚读到您(6月6日)就秘鲁经民主程序选出新总统后的感言:“我们不会回复到贪腐和血腥的独裁政权,可喜可贺。”
可同时,我怀着忧虑读着中国媒体上对您中国之行的预告。据报道,您将在中国获得“荣耀性”的待遇,如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研究员”,您甚至将被邀至中国国家权力的象徵地,也是人所共知的御用国会殿堂──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这恐是中国官方能给予作家的最高演讲场所了,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我不记得有哪位作家曾受过如此的尊崇。容我直言,您或也清楚,这个给您如此高尊崇的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
我相信,以您的作家之眼和对独裁体制的认知,您多少已知悉,您将踏上的这一伟大国家正处在自1990年以来人权最黑暗的时期。近半年来,已有近百位表达了政治见解的作家、知识份子、律师相继遭到短期或长期“被失踪”式的拘捕。举个例子,那位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自4月3日早晨於北京机场被秘密逮捕迄今,中国警方连一份正式拘捕文件都未曾向他的家人出示过。
您也会记得,在您踏上中国的同一时间,您的国际笔会同人,和您同一年,即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仍在狱中,他还有着近十年的牢狱生涯。而另一位来自中国的作家,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近十年来,他不仅从未收到过中国的大学、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学邀请、荣誉职称,也不会享受到您将在中国获得的那些殊荣了。
我曾拜读过您2010年12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您在文章中探讨了我们时代的困境以及独裁体制对於人类和文学的伤害。此刻,我对您的这段话记忆犹新:“……非常遗憾,民主国家的政府非但没有跟那些勇於同独裁政权抗争的人(比如,古巴的‘白衣妇人’、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昂山·素姬和刘晓波)站在一起,把他们的抗争当作共同的事业,反而经常跟迫害这些勇士的政权达成默契。这些勇士不仅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也在为我们的自由而战。”
可以想像,此行您将会与许多中国官方安排的作家如王蒙、莫言、铁凝、阎连科、余华等人见面,他们会提出引人深思的看法,您和他们会有相同和不同的见解,甚至会有不失尖锐的对话。
正因为此,我强烈地建议您,在您这次中国之行的公开演讲中,应该直截了当地向接待您的中国官方机构、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您的中国读者、作家同行及研究您着作的中国学者陈述您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表达的那些真知灼见。因为您是一位作家,您处在比政治家更自由地表达见解的位置上。您甚至可以以自已受到独裁者暗杀威胁的经历,开诚佈公地探讨作家也会有的怯懦。他们虽然未必有着您的勇气,可出於对您的敬意,他们或会因为您的直言不讳而深思。
就像十多年前我建议苏珊·桑塔格要尽早再访中国一样。我想强调,您应该去中国,而且不仅仅是去北京和上海,您应该去更多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甚至踏上西藏。然而,您不应被动地接受中国官方为您提供的安排和行程。
也因为我读到了您在获奖演说中谈到您母亲的那段话:“我希望我母亲今天能在这里,她是一位会因为内尔沃和聂鲁达的诗句潸然泪下的女人。”所以,我想向您介绍另一位母亲,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女士,她是已故中国诗人艾青的妻子,而艾青与聂鲁达是好友。我真希望您在北京时能和她见上一面,我甚至想建议您,应该去探望一下被软禁在家已八个月的刘晓波妻子刘霞。
具体一点说,您在北京期间,假如有两、三个小时的空闲,您和您的翻译可以在下榻的旅馆前,或在半路上拦住一部出租车,递给司机一张用中文写着她们北京住址的旅馆便笺,直接前往她们的家。当然,您是有过独裁体制下应对经验的人,而且曾经应付自如。或许,您会被便衣警察在半路阻止,或被挡在她们的住所之外,甚至,还会让您无法坐上出租车。可这一经历足以让您了解中国的专制统治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上海及北京期间,除了官方媒体上公佈的您与中国作家协会(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及掌控的作家组织)会员身份的作家见面对话外,我也建议您能和体制外的作家见面交谈,如在上海的作家韩寒、在北京的小说家康赫、作家王力雄和诗人唯色夫妇。经由译者,这些作家会向您呈现他们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思想。
我的这封信并非要扫您兴,而是希望您的中国之行可以“尽兴”。这或会使您的中国之行多了些“惊险”,可是,这不正是作家的部份天职或天性吗?仅仅从象徵的意义上,这些举动将向广义上的中国知识界,向在狱中或可能入狱的中国良心公民,甚至向世人,传递明确而毫不含糊的讯息。
在您即将或已踏上中国之际,期望您能读到这封信。
您诚挚的
贝岭
2011 年6月11日
——————————————————————————–
[1]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1936年3月28日-),台湾译为尤萨。持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1993年7月2日取得西班牙国籍)的作家及诗人,也是从政的政治家。创作小说、诗、剧本、散文、文学评论及政论文,也曾导演舞台剧、电影,主持广播电视节目。尤萨的小说技法诡谲瑰奇、丰富多样,其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因“他对权力结构的描绘,以及对反抗、起义、失败的犀利洞察”获颁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1年2月3日,西班牙国王颁皇家Real Decreto 134/2011号令,获封巴尔加斯·尤萨侯爵(Marquesado de Vargas Llosa)。
[2]娜汀·葛蒂玛(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南非小说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纵览中国》首发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