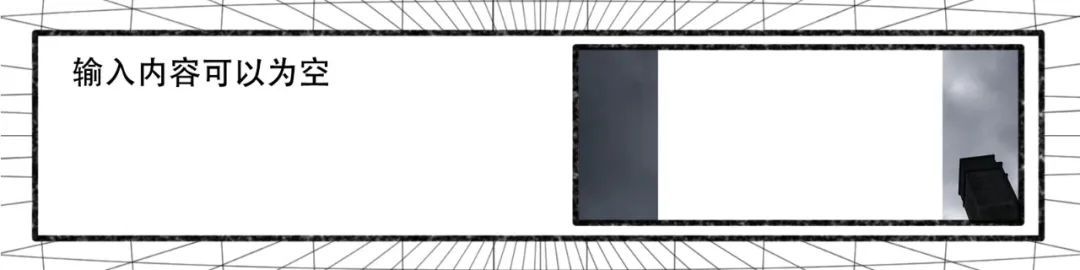行程卡下线了,但还有不会下线的摄像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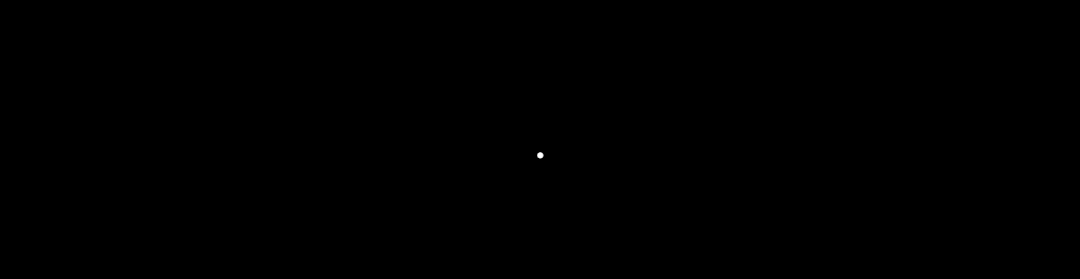
图片:虾、沉吟、胶泥、戈达肥肥、芥芥子
作者:芥芥子
编辑:芥芥子
引言
12月12日,通信行程卡的公众号发布了消息:“12月13日0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通信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app等查询渠道将同步下线”。随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相继发布了删除行程卡相关用户信息的公告。至此,大疫之下运行了三年的行程卡,突然间走到了历史尽头。行程卡的下线,也引发了民间对于健康码、核酸码、场所码等疫情防控期间的大数据管理工具尽快一道下线的呼吁,一时间,例外状态似乎要到了尽头,以疫情防控目的的公民信息追踪可能也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在疫情之外,是常态的生活;在非常态的数据追踪系统以外,还有常态的数据监视系统:本文即以摄像头为契机,反身性地回顾日常生活中的监控与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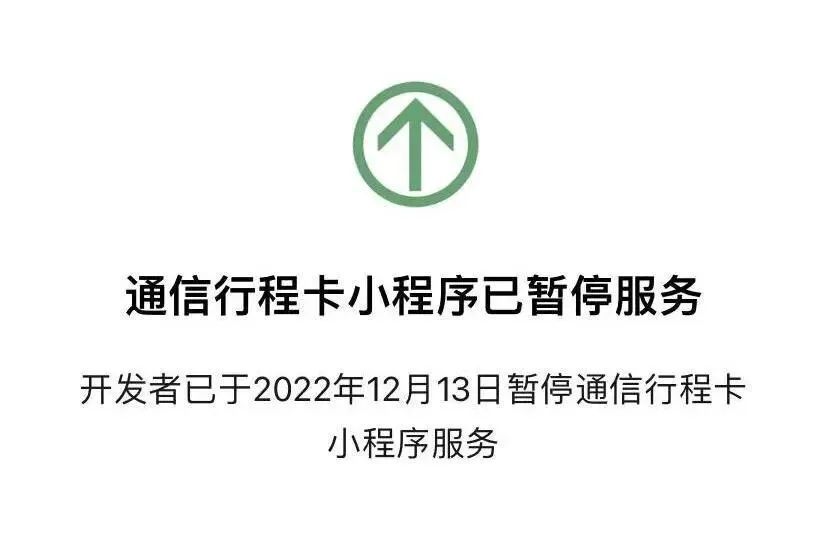
嵌入社会的摄像头
2017年,艺术家徐冰创作了其首部影像作品《蜻蜓之眼》。
他收集了上万个小时的监控录像,通过选择摄像头视角下庞大的视频影像数据库,拼接成一幅巨大的画面,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男女的爱情线,藏在由视频资料描摹出的社会的众生相里。正如徐冰所言:“今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

摄像头嵌入社会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嵌入社会的摄像头,从金盾工程中起步,伴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于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的立项和扩建,最后融合于现在的网格化管理。
90年代,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被提上日程,经过一期工程(03年起)和二期工程(06年起)的建设,摄像头初步在各大城市的主要空间上铺开,此时的监控建设仍比较粗糙,设备也以进口为主。
在进行了初期的铺垫之后,以城市治安防控和城市管理为宣传,在“平安城市”的口号下,天网工程(2007)拉开帷幕,由于国内的技术进步,海康威视、大华、宇视等企业的迅速崛起,摄像头设备逐渐完全国产化,并和人脸识别算法相结合,升级为新一代监控系统,逐渐全面覆盖国内大中小城市;在2016年,在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背景下,“雪亮工程”开始推行,重在放在了乡村地区等“薄弱环节”,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全覆盖、无死角,达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目标,进一步将监控的视域扩大。

在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推进的平行线上,则是被近年来高度重视的网格化治理的推进。网格化治理被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将社区分割为一个个网格,每个网格在300户~500户左右,被分割后的社区,变成了一堆堆高度可视化的细小空间,伴随着无死角覆盖的摄像头,终于完成了拟态世界构建的最后一块拼图。
早上醒来,走出房门:欢迎来到一个被审视的世界——藏在光鲜世界的阴影里。这个“拟态世界”的基本元素,即由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形态各异的摄像头组成,无时无刻的,通过镜头,这些异世界的元素记录下来持续的时空,并维持着这个拟态世界的运行。
安全、自由与隐私:被选中的与被放弃的
在霍布斯《利维坦》所阐述的自然状态里,存在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人活在恐惧之中,而处于对混沌和暴死的恐惧和对安全的希求,一切人都让渡出了自己的权利给一个主权者,而这样的契约也促成了国家的诞生。
不论是行程卡的推行,还是摄像头的大量普及,也出于类似的原由。
正因为此,安全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优先目的,以安全为名,成为了宣传中的话语主导。在官方的语境下,以摄像头为基础的监视系统是为了治安管理的目的,为了迈向一个更“安全”的社会,而推行这样的政策,则被视为一项政府的善政。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大幅降低了犯罪率,在媒体的宣传里,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因而另一方面,群众往往也乐得接受这样的话语体系,安全来自于身边的体验,也来源于宣传中的大国想象,在宣传与体感的交融中,安全成为群众服膺的首要价值。

然而现实并不会只停留于此。霍布斯讨论了民众出于安全的目的让渡权利导致了利维坦的诞生,他所没有讨论到的是,当国家这一利维坦获得了生命之后,国家成为了自我的行动者,同样也诞生了危机意识——即对安全的意识:国家不仅会保护民众的安全,自主性的国家,还会有意识的保护自己的安全。因而安全一词,在现实世界的运行中,实际上混杂蕴含着民众的安全,与国家的安全两重意义。更为现实的是,两者在某些时刻是可能产生冲突的,在此时,后者将具有比前者更高的优先级,因而当两者出现冲突,当维护稳定成为需要时,可能会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我们可以看到,在烂尾楼事件、银行事件、乃是各类群体性事件所导致的抗议中,监控体系往往充当了消解群众安全的工具,通过快速的定位,将“不和谐的声音”消解在萌芽之中。在此刻,推广摄像头的多重目的,也从单一的维护民众安全的叙事中脱离与表露出来。
在被选中的安全之外,则是被放弃的自由与隐私。
自由与隐私,实际上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当隐私被削弱,同样被削弱的也是自由。当人脸识别成为了进入小区的必要凭证,当无死角的监控覆盖了大学校园,隐私已经不复存在,公共空间也带上了完全不同的属性,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被消解,原子化的个体被还原出来,在敞露无遗中,维持着虚幻的自由假象——间带着安全的想象。在常规状态下,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以为他们是安全的”,这种平静也许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这种非对称的关系并不是永久的:利维坦诞生于恐惧之中,也活在恐惧之中。因而关于后者意义上的安全,会一直膨胀生长扩张下去,并不停歇地挤压前者的空间。这预示着,现实破碎的一天,在终点等待着每一个沉默的个体,正如那句老话说的,“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的人,往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摄像头的在场与权力的隐秘运行
2016年,葛宇路曾完成了一个叫《对视》的实验性作品。

在街边选择了一个摄像头,葛宇路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视,直到背后的监视者线下出现。葛宇路在接受央视《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在这里,我质疑的是一种监控的权力。我对它并不能做出实质的改变,我只是盯着它,争取盯几个小时把背后看我的人看出来,或者说我们之间能够有一瞬间的对视,我觉得那就很棒了”(新闻周刊,2020)。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被看者成为了观看者,观看者成为了被看者,通过这一短暂的权力关系的倒转,葛宇路也揭示出来了常态情况下权力隐秘的运行方式。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新的监视形式进行了研究。他对边沁的全景畅视空间进行了发掘与描述,在这样的空间中,囚犯只能被看,不能看到观看者。最终,权力从这种制度设计的毛细血管渗透下去,成为一种遍布社会的微小网络。在当前,随着国内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和国内网格化治理的推进,遍布大小城市乡村,遍及道路、广场、学校、医院、公交、公园……几乎在任何地方,摄像头都完成了在场。摄像头多数时候是难以识别的,隐藏在树荫下,隐藏在墙檐下,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但即使不被观察到,人们已经内化了它的存在,而这种内化也将无形中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对于行程码的监控原理,人们大致了解,但对于摄像头背后的监控方式,人们则未必清楚,甚至兴趣寥寥。然而,不会下线的摄像头,和我们的生活更为紧密,也可能会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肉身不仅在现实世界中被异化,还被监控、被定位、被识别、被重组,被传送到了摄像头建构的拟态世界中,成为运作中权力的营养套餐。
摄像头存在于微观不起眼的地方,反过来,正提醒我们权力的微观性质。它弥散性的存在于社会中的各个角落,牢牢地嵌入社会之中,它无时无刻的运行,也提醒着我们权力流动的性质,也提醒我们权力不止是高高在上的,它可能还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可以是无声的,可以是隐晦的,个体则受到这种权力持续不间断的影响。
在这样的拟态世界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再回顾行程码。大疫三年里,行程码对防疫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针对例外状态所开发出来的大数据追踪监控工具,也在限制人身自由、管制人口流动等方面存在大量被滥用的情况,造成了不少恶劣的影响,所幸的是,由于群众的呼声所导致的例外状态的终止,行程码也连带着走到了尽头。
我们乐见行程码的下线与个人数据的删除,它维护了公民合法和正当的权利。但值此行程码下线的契机,应当对例外状态之外、我们常规状态的生活进行更长远的反思,对更加宏观的以公共摄像头为基础的数据监控系统,进行更审慎的思考。

*联系我们/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