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按摩女日记:我去华人的“大保健店”面试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BIE别的 ,作者BIE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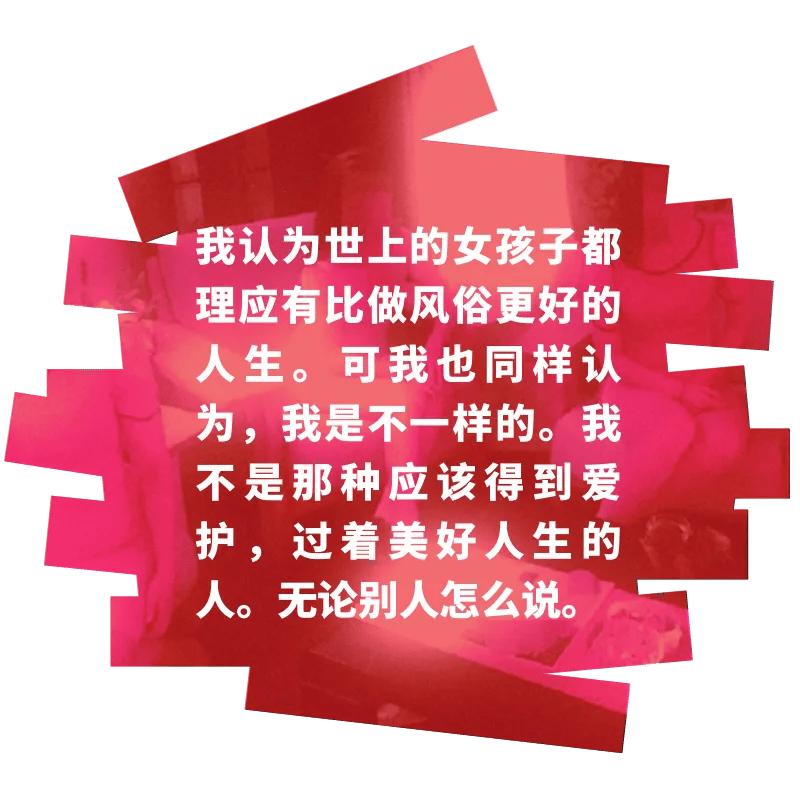

从两年前开始连载「在日女子日本红灯区漫游指南」到现在,这个系列已经累计发布了十余万字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后的一个重要篇章,「东京按摩女日记」系列。
世俗上来看,作者的这段经历不仅说不上光彩,甚至连错处都有好几种说法。但当她跟我说她要去按摩店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早晚会把它如实纪录下来,然后像从前一样,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去看。
那段时间,她总是跟我讲些在按摩店遇见的新鲜事,通常是开心或有趣的事情,而我一边担心着她的人身安全状况(却帮不上什么忙),一边已经在忧虑当她把这段经历变成文字时,我又会看到哪些不便启齿不够愉悦的经历……当然,我更担忧的还有发布后可能遇到的审/查风险与舆论攻击。
不过,这个故事可能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刺激。不仅不够涩情,甚至也不如人们期待中的失足女日记那样悲情和猎奇。
这只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人,她在东京某家 “大保健店” 工作,一天要给十个不认识的男人手冲的纪实故事。这是她的故事,也是世上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故事之一。如果你的道德警报狂响,那恭喜你正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这很好。就像作者说的,你们都理应有比这更好的人生。2022 年伊始,一个漫长的冬天即将结束。
在这个冬天,发生了三件比较重要的事:我在日本顺利递交上了我的修士学位论文,我度过了自己的 25 岁生日,和开始了我在歌舞伎町的最后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在新宿歌舞伎町的一家华人大保健店,给男客人用手打飞机。说得更文雅一些,就是回春按摩。
当然,这是一家非法店铺。它的招牌上写的是中华按摩,前台贴着一大堆针灸穴位的海报。如果有不知情误入了这里的女客人,就打电话喊来其他店的按摩师傅,在前台附近的按摩椅边给她们做普通按摩。但我,还有店里其他来自中国,缅甸,越南的女孩子们,我们真正工作的地方,是一帘之隔的店铺后面。
01 华人互助论坛
从来日本的第一天起,我就和歌舞伎町接下不解之缘。在去按摩店前,我在同一条街上做过陪酒女。陪酒女和风俗女的差别是什么呢?借用当时我陪过酒的店里一位前辈的话来说,“陪酒还好,但绝不要堕入风俗。”
就连陪酒的女孩子都会说风俗很可怕。
但在我陪酒之前,我想做的确实就是风俗,陪酒反而是最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件事也在之前的系列里说过了。我想当风俗女却没有成功,完全是因为歌舞伎町严格的管理条例。哪怕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在律法整顿下,现在也没有一家风俗店敢非法雇佣外国人的。
我有一个专门用于夜职的推特账号,也用它来找过很多很多风俗行业的中介,日语称呼为 スカウト ,加了无数人的 line 。也曾有人承诺,如果愿意去外地出勤,或者满足更苛刻的出勤要求,就可以替我想想办法。但最终连这些职业中介,也没有一个人能找得到愿意收我的店。
会来到这家华人开设的大保健按摩店,也是迂回。某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条帖子,大意说的是,一个在日女留学生经语言学校的朋友介绍,去中国人开的奶茶店打工,到了才发现是风俗店。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她好不容易才逃脱。
我知道这么说很奇怪,在看到这条微博后,我第一反应是幸亏她逃走了,第二反应是我想去那样的店工作却找不到。日本大大小小的风俗求职网站我都看过,我和无数夜职圈子里的日本人打过交道,然而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不了解在日华人的圈子。出国留学前,一位前辈告诉我,出了国后一定要提防打着老乡名头,对你过于亲切的国人。然而我没有在语言学校待多久,到了日本以后立刻就去读了研究生,还进了一个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大学,反而没有实际接触过几个在日本的中国人。
最多的接触,只有偶尔几次去过新大久保的华人物产商店。新大久保还残留着十几年前的味道,我是指类似于成龙的《新宿事件》里那样的味道。街上鳞次栉比的都是汉字招牌,在这经营店铺的都是最早几批赴日华人,有的连日语也说不明白。那些很早就来日本的中国人不同于现在的赴日留学生,有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圈子。
我也听人说起过,日本人开的风俗店现在都怕了警/察了,敢顶风作案的,只有中国人开的非法风俗店。价格低廉,连很多常去风俗的日本人也不敢去这种店。
为了能去干风俗,我在网上搜索了 “在日 华人” 这几个关键词。意外地,被我找到了一个在日华人互助论坛。
打开一看,入眼竟是许久没有见过的古早味网页设计,但论坛里的内容却依然以分钟为单位快速更新着。这个论坛里有很多板块,最活跃的是招工信息板:有招搬家工人的,有招奶茶店员工的,还有在贴名标注 “招女孩” 的 —— 也就是我现在在寻找的那些非法风俗店。
这中间也分为好几种,其中一种是“公寓型”。我看了一圈才搞明白,他们租下都内十多间公寓单间,每个公寓房间里配置一个女孩,客人直接上门去公寓里。他们压根就没有店铺和办公室,更没有取得风俗业店铺经营许可证,这样一来就完全绕开了日本的所有法律 —— 连找都找不到,更别提上门查人了。
另一种则是隐晦的 “店铺型”。开一家全是女技师的按摩店,而实际上提供的是 “ 回春按摩”,和国内的大保健一样。
从常识上讲,我也知道第一种明显危险得多,不过但凡是正在招工,距离合适的,我全部加了联系方式,然后逐个打电话联系。基本上他们也不用我提供别的什么,只要了一张自拍,就算是初试。我的长相,哪怕是精心化了妆后,混在新宿的街头都是个丑女。但一家 “公寓型” 风俗店的老板却回复我:你这么漂亮,一定能赚很多。
他问我,之前陪酒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多少。我如实告诉他,他却在听到我报出的数后笑了,然后告诉我,在他那一天就能赚这么多。
02 我需要钱,我要活着
在开始这个系列之前,我曾收到过编辑的提议:对于无法绕开的 “为什么去做风俗” 这一话题,为了规避风险,也许可以包装成 “ 一次田野调查 ” 。
可事实不是这样。我真的并没有那样高尚的念头,我会来到红灯区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来的时候,是为了爱,或者说,为了寻求认可。很好笑吧,因为我太想被爱太想被需要所以从十八岁时就梦想做风俗。那是我认为我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途径。
我天然地对自己去做风俗这件事没有心理负担。我认为世上的女孩子都理应有比做风俗更好的人生,可我也同样认为,我是不一样的。我不是那种应该得到爱护,过着美好人生的人。无论别人再怎么说,在我自己的心里,我并不值得那些正当与美好的事。我是不同的,更低下的生物。如果有人愿意买我这个垃圾,无论是以什么形式,我就该知足了。即便是我,在拿到钱的那时一定是有价值的。钱就是最好的,不会说谎的证明。
可能我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在这个社会上是罪无可赦的。这完全是一个自找的故事。
而且,我现在真的很需要钱。我以前也需要钱,但并没有那么急切。简单来说,我现在这么需要钱,是因为我突然无比想要活下去了。我以前老是觉得,自己反正很快会去死,从没认真考虑过如何活下去。当陪酒女时赚来的钱,也全都给牛郎了。
我原本计划毕业前就死,因为活不下去,我还为此做了一张清单。但是,总有意外,现在我可以活下去了,因为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突然找到了一条活下去的路:三个月后我会回国,然后,我会彻底离开我长大的那个家,可以从二十年的噩梦里逃走。我会删掉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去很远的城市里躲起来。至少有朋友愿意为我提供住处了,虽然我依然找不到工作。
我总以为我过着很普通的人生,但是好像从某一刻起,我的人生就脱轨了。那到底是哪一个时刻呢?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是终于开始吃药的时候,还是大学被教师性骚扰于是不敢去上课的时候,还是被生母拉着一起企图自杀的时候,还是小学在寄宿学校里被同学与教师一道欺凌的时候,还是说,某个与这些都完全无关的,没有任何象征性的,生活里很普通而平淡的一刻呢?
我自己也不明白。意识到的时候,好像我就离正常的生活很远了。我以前想着,没有关系,我可以去死。但现在纵使我能活下去,我却也无法像个“正常人” 那样理所当然地活下去。就好像我和这个世界的卡口,已经哪里都对不上了。
我的体力很差,生病的时候动不了也不敢见人,好几年的时间里,只是像雕塑一样待在静止的房间里。活到二十五岁,我甚至没有实习过,再加上精神障碍,大概连残次品都不是。
现在我突然想活下去,而起始资金是零。人在世上活下去需要多少钱呢?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但我却被一种变态的焦虑所控制着,我只知道,我要很多钱,这样才能安心。我只知道……就像很多女孩和中介说过的那样,去当风俗女,是为了去赚这个年龄段才能赚到的钱。只有在二十多岁时我才能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换钱,过了这几年,我担心自己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了。
有人告诉过我,别这么想,你现在还小,但等你工作了几年后就会发现,人长大之后要赚几千块一万块压根不是那么难的事。可那时的我根本无法相信这话,只觉得是安慰人而已。
现在开始我得努力做个大人了,我心想。当大人就是要做很多很辛苦的事的。
03 神秘的华人大保健按摩店
晚上八点,我按照微信上传来的提示,去了新宿车站附近的按摩店面试。
此前在微信上和我联系的,就是这家按摩店的老板,是一个面相斯文,年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说是老板,实际上应该是被雇佣来的经理。按照我对红灯区的了解,这些店真正的老板往往不会自己出面。我提前按照他给的地址搜索到了这家店的信息和照片。映入眼帘的,是颇有冲击性的中华土味图像,以至于很难想象这是在日本,感觉更像东莞(虽然我也只在新闻上听说过东莞)。

店内的光线其差无比。棕色的廉价地毯,诡异的大理石桌面上放着茶楼款的全套茶具,还有弥勒佛和木牛,桌边的椅子是奇怪的雕花木椅。一道中式花窗屏风上挂着脏兮兮的欧式挂帘,这后面便是女孩们迎客的地方。在下一张照片里,女孩子们画着日本早就不流行的妆容,穿着不合身的艳粉色紧身连衣短裙,墙角还有一座格格不入的希腊风石膏像。以上这一切混搭在一个六十平左右的空间里。

我甚至还在这位经理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些 “企业文化”宣传。比如新年的时候,这家大保健店推出了印着 “ X 氏综合株式会社” 字样的自动笔,和中华特产凤梨酥一起随机送给到店的客人。此外,还有在妈祖庙开过光的 “ X 氏株式会社” 的纪念金币等……一番探索下来,我算是大概搞明白,这个大保健店的实际所有人是一对几十年前就来到日本的闽南夫妇。其中,X 氏夫人,现在的年纪应该算是奶奶了,开了许多按摩店,当中也包括大保健按摩。我要去的这家大保健店就以这个姓氏命名,墙上甚至还挂着这位 X 奶奶的照片。那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经理自称也姓 X ,不晓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
听说,早年间许多来日本的福建人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后来则是被来自东北的另一群人所替代。虽然这些故事已经是过去的都市传说,但这家按摩店的背景确实是有些神秘,让人再次联想到电影 《新宿故事》 一类的,我也说不清他们和传说中的 “华人黑帮”有什么关系。
这么说有些轻浮,毕竟这是一个风俗女的自述,在人们眼里应该更悲惨和痛苦一些。不过,可能是我天生神经比别人少一条,我不能否认,无论我如何想以一个严肃的态度叙述这个故事,当发现这个神秘的 “ X 氏 ”的时候,还是多少有点 “电影情节竟然发生在我身边” 的兴奋。
以至于,我连夜斥巨资 2000 日元买了一只录音笔 —— 造型是钢笔,有摄像头和录音功能 —— 别在包包上去了面试。现在想想可能是有些夸张了。
但无论如何,我想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
店铺在新宿车站出口不远处,并不在歌舞伎町红灯区,而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一路上都是些普通的小饭店,因为距离车站很近,所以相当热闹,晚上八点依旧人来人往。走过两个路口,从一家便利店侧边的狭窄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我估算了一下如果遇到什么……我就逃跑。距离很短,跑出门并不困难,并且我开着摄像和录音。像这样想了一下,我整理了一下着装,然后推门,朝已经提前在谷歌地图上见过的大保健店走进去。

04 大保健店面试实录!
下文中出现的对话内容,均为录音笔记录直接转写文字
2022 年 2 月 6 日,晚上 10 点 09 分,新宿某丁目,X 按摩店
先招待我的,是穿着白衬衫,黑马甲,一身酒保打扮,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的一个中国女人。她在前台负责接待,看起来就是这个店内的“妈妈桑”。她看起来非常亲切,肤色黝黑,头发简单地梳着,也没有化妆,就和平时买菜时会遇到的所有中年妇女一样。
她看到我,招呼着,“哎呀,好漂亮。”
“诶,哈哈,谢谢……”
“真好看。一会儿老板过来啊,你先把包放一下,稍等一会儿。要不要喝点啥?”
“没事,不用了。我有点紧张……”
在进店的一瞬间,我就已经给自己编好了一套 “人设” 。我的 “人设”,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学生,家境不算好,以前都是乖宝宝,在此次 “误入歧途” 前完全不了解红灯区的事。期望着这样一来,对方也更能对我放松警惕。
妈妈桑热情招呼着我,一边摆着手让我放包,一边亲切地关心着,“哪里人?你不要紧张。”
“那个……”我报了自己真实的出生地。因为我对外地的风土人情都不熟,怕被问出马脚。
“ □ □ 人啊?哎呀,这里很少的。“
我傻傻地陪笑着。妈妈桑又问,“来日本多久了?”
“两年,快三年了。”
“哦,那刚好疫情的时候你来的。”她一脸那真辛苦啊的表情。
“嗯,疫情再往前一年,应该三年了。”
“哦……那还刚好是……”
我们面面相觑地笑了。
“上学?”
“嗯对,上学。”
说着的时候,店里另一个姐姐路过,接着我们的话头寒暄了两句,说起我家乡的事。似乎,流落异乡的人,总会先就着这个话题熟络起来。我们在遥远的东京,说起了海那边的城市。
妈妈桑又问,“多大了?(看起来)很小。”
“二十五。”
“才二十五岁啊……”妈妈桑说。那个加入寒暄地姐姐也看着我,认真点头:“看着就小。”
—— 事实上,在我平时生活的学生圈子里,二十五岁已经比很多人都大了,网上的很多人也喊我姐姐。在歌舞伎町工作的日本女孩,也大多比我年纪更小,从十八岁到二十岁刚出头。二十五岁的,很多都是已经混出名气的陪酒女风俗女了。但在这个店里的姐姐们看来,我完全还是一个小姑娘。她们看起来大多是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往上了。有的人的年龄,甚至能做我妈妈。
妈妈桑:“对呀,看着像二十岁似的吼。”
我不好意思地笑着。
妈妈桑还是感叹着,“才二十五岁……真小。”
—— 后来在这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风俗业,尤其是我们这种低端风俗业,年龄小可以说就是一切。我在同龄人里绝不算漂亮的,技术也没有那些姐姐好,更没有其他人“会来事”,但年龄小,在这里就是最大的优势。
好像客人们只要看到我的年龄,就会立刻点我似的。买一个年纪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女孩子,对他们来说仿佛就已经是一件足够“体面”,足够爽,足够满足虚荣心的事。我好像能理解人是会这样想,却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个子好高,有没有一米七?”
“有一米七。” 我点头。
“真好。” 妈妈桑说。另一个姐姐接话,“她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个子很高。”
“其实我今天穿了高跟鞋。不过好像日本人都不喜欢太高的。”
店里的姐姐正色赞同,“对,你以后不用穿高跟鞋。”
“嗯……”
妈妈桑:“很挺啊,看着就好。”
姐姐:“我现在看到二十多岁的就羡慕……“
妈妈桑:“你眼睛都放光了!”
大家笑作一团,我夹在里面,总觉得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或者说是有些奇妙的愧疚。
正笑着,店长就进来了。是穿着西装,梳着背头,一口南方沿海地区口音的年轻男人,也就是之前我在微信上联系过的 X 先生。妈妈桑向我介绍,那就是店长,然后用带着奇怪口音的日语对店长说晚上好,另一个姐姐也是一样。
“这么高!”
店长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妈妈桑和姐姐热情地打趣着:“对呀,都和你有得一拼了。”“你们比一下,比一下身高。”
又是一番关于身高和我的出生地的闲聊,还有感叹我年纪之小。店长的态度明显沉稳很多,他走到大理石桌的后面,让我在前面坐下,我们中间间隔着那套在店里显得非常格格不入的紫砂茶具。妈妈桑热情地给我摆好了外套和背包,然后和店里的姐姐去后面忙了。
“来很久了吗?”店长问。
“来了三年。”
“三年。在读语言(指语言学校)?还是专门(指职业学校)?”
“在读大学院”
“在读大学院啊。”—— 看起来这在他的店里很少见 ——“以前在国内是读大学的?”
“对,大学毕业了来这里。”
“做什么……哦不是,是学生,学什么的?”
我模糊地回答了,不过和事实没有相去太多。
“那你在中国是在哪儿上大学的?”
“上海。在上海读完大学,然后来日本了。”—— 这是假话。
“来日本挺好,挺好的。”
期间夹杂着客人往来,妈妈桑用日语打招呼的声音。说实在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应聘按摩女,要如此详细地问我的学历。可能是为了掌握我的情况?虽然我也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总有一种本能,就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
“多大?”
“二十五。今年刚二十五。”
“你现在那边还有在上吗?”
他说的是我之前在微信里和他提过的,虽然我没做过风俗,但是在日本人开的 Girl's Bar 里工作过的事。
“那边没有再做了。”
“之前那家店在哪?”
“在歌舞伎町……叫 '东' 的。”我大概报了位置和店名,反正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然后故意露出尴尬的笑脸,“不过那家店比较便宜,也没什么人去。”
老板对那条路倒是也很熟,哦哦嗯嗯地点着头,并不意外,还问了我是哪栋楼,几层。然后问我,“那他们那边给你多少钱?”
“他们那边是底薪很低的,主要是算一杯酒的 パック (指回扣),这样算。”
“嗯,现在那种不好做了。”
我讪笑着,“确实。”
“现在疫情,人少了。” 老板接茬说道。不过说实在的,疫情对于陪酒店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反而在疫情状况下,日本其他居酒屋不营业,来廉价陪酒店喝酒的客人还略多了些。
当然这些话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扮演的是一个初入红灯区,有些不安,又急需钱的单纯少女 —— 我赶紧抓住话题,低声地,“对……我就是觉得,在都是日本女孩子的店里……而且我光会陪酒,就竞争不过别人……”
“但你日语反正很好。“
“也没有很好……也就是说话没什么障碍。”
“但你读大学院啊,平时要写论文吧?”
“要写的。”
“你什么时候毕业?”
“明年吧。”
“然后呢?接下来做什么呢?”
“后面……还不清楚。我想在日本找工作,但不一定能找到吧。” 我苦笑着。
这句当然也是假话,三个月后我就回国了。不过,如果说了实话,我怕我很难拿到这份工作。夜职界最怕做不久的人,虽然其他行业似乎也是一样。
我总是在说谎,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条街上,面对不同人的脸,我总能像呼吸一样自然地说谎,呼吸一样地摆出各种表情。我在歌舞伎町报给所有人的名字都不一样,所有经历和出身都不一样。一开始还可以说,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有时候甚至是觉得有趣,但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这种时候真的有必要说谎吗?有时候,我也会突然感到困惑。
他顺着我的专业,语气冷淡,却又说了好些文科生以后要在哪就职啊之类的话。意外的,就像一场普通的寒暄,好像我们根本不是在进行风俗店的面试,他只是一个先来日本的前辈而已。聊了一会儿他才问,“你是在哪看到我们店的?”
“是在那个华人论坛……”
“论坛?”
“对,论坛。上面有各种招工的,我点进按摩招工的,然后就……”
一直没有什么表情的老板咧嘴笑起来,“对这个有兴趣?”
“对,就那个,有朋友推荐我去做男士按摩……” 我故意说得比较磕磕巴巴的。
“嗯……”他沉吟着。
我尴尬地笑着继续,“但因为我的签证,就做不了日本那边的店嘛。于是就找了一下,找到了华人那边的。”
“嗯嗯。”对方依然是刚才的表情,“那对你现在来说,收入大概多少可以够?”
来了,最经典最重要的问题。
“呃……可能主要还是看这边的排班。”
“这个看你自己。你要上几天?”
“我现在还在上课……”,我有些迟疑地说。其实这还是假话,我都已经通过答辩,就等毕业式了。可我现在还不清楚这家店的底细,不敢轻易承诺。
“你上课是白天?”
“嗯,一般是上午下午都有课。不过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寒假了,可能寒假之前我每周做个三四天,寒假之后基本上都 OK 。”
“学校在哪里啊?”
“我学校在那个……”我不好意思地笑着,“早稻田。”
这句当然也是假话。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并不大,这是一家背景不明的中国人开的店,我怕他们有什么渠道能找到我。
“早稻田?这么厉害。高田马场的那个?”
“嗯,对。”
“那还挺近的。”
“不过我住得远,高田马场附近的房租还是有点贵。”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高学历啊。”
“没有没有。”
“然后你现在来这边的话,晚上就是做到末班车咯?”
“对……”,我说着掐指一算,突然想起一件事,“不对,我下周起就都可以来了。”
似乎是被每周上几天班、每晚上到末班车的话给提醒了。我突然想起,我需要很多钱。我其实没有太多时间用来担心害怕了,于是赶紧换了话术,表示自己可以多加些排班。
“那挺好的。” 对方点点头,“那今天让你来,也就是给你先看一下,我们这里是这个样子的。更了解一下的话,我们这里一个套餐是一个小时,基本套餐是六千 (日元,折合人民币 300 元左右),推油的话是九千(日元,折合人民币 450 元左右)。然后一般来说,客人只来一个小时的比较少,平均都是在两个小时,一万到一万三(日元)。“
我点头如捣蒜。
对面继续,“然后呢,我们这边和员工是对半。没有其他的,就对半。一天的话,可能平均 —— 尤其是新来的话,新人都会比较有人气。像你这样新来的,一天两三万是有的。”
一天两三万日元。
老板说得一脸平淡,我却已经被吓呆了。一天两三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天一千多入账。当然,这大概是骗我的,我心知肚明。赚多少完全取决于多少客人,反正也没有底薪。他大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这是风俗店招人的基本套路了。
但我还是被吓傻了,我这种人,会有人愿意花一千多买我?买我这么丑的脸,这么丑的身体。你们这些人没事吧?简直想如此大喊 —— 这可是真金白银的钱啊。何况,说到底这只是性感按摩的价钱,甚至没有做/爱。
我第一次去援/交的时候,比现在更年轻,还是标准的女大学生。我还没有和人牵过手,没有谈过恋爱,没有性经验。那时给自己开的价格,也只敢开到三百块人民币。因为我从小就是丑女,黑皮肤小眼睛,头骨的形象像猴子。小学的时候,如果有男生敢和我说话,就会成为所有人嘲笑的对象,女孩子也都不愿搭理我。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丑女。那天,我画着妆,穿着自认为最漂亮的裙子,和客人在地铁站见面,心里雀跃又不安。
然而,约好的人来了,走下车关了车门,只站在那打量了我的脸一眼。我讪讪笑着说得先给钱,三百块……不不,只先给一半定金也行。那个男人看了眼我的脸,什么都没说,掉头就走了。
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那人看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只记得那辆车在视野里远去,只有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那是一个暑假的午后,下午三四点,太阳很好,银色车尾巴在金色余晖里闪闪发亮。虽然不记得那人的表情了,但大概是被吓到了吧。一脸厌恶的,觉得我太丑了,被路边突然出现的丑女吓到的表情。
应该是三百块也不值的表情。
我出生在一个经济发展还不错的小城市,那时的三百块钱,在这里,能干什么呢?能吃一顿日料自助餐吧;那天的车站不远处有个游乐园,学校带我们来这春游,我小时候那里的门票是九十八元,现在是一百九十八;大学生难得出一次门放风,两人买两张电影票,再吃个饭喝个奶茶,两人花的加起来也有三百 —— 三百块也没有那么多吧?我可是在和援交比啊?!
但,冷静一想,也对。我自己,和吃一顿自助餐相比,和玩一次游乐园相比,和与人一起看一场精彩的电影相比,我这个人,这具肉壳,好像也真没有能比得过的价值。放在案板上的我,和放在案板上的三文鱼寿司相比,三百块可能是有点太多了。
“嗯……嗯嗯。”我坐在东京的大保健店里,面对着一脸平淡却开口就是你一天能赚两三万的老板,努力不动声色,但还是有些呆滞。算了,也好,反正我的人设也是一个对风俗业不熟的女孩。
老板继续着,“我不知道你以前在那边赚多少,反正……”
“之前一个月赚了八万(日元)。” 我突然很快地接话,接完才觉得不大好,“……没有一个月,小一个月,赚了八万多吧。”
“才八万多?”
“才八万多。” 我梗着喉咙继续,然后不好意思地笑笑,抬高了声音,“因为竞争不过日本女生,哈哈。”
“也太少了。”对面乐呵呵地。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去很多时间。”
“这边的话”,老板悠悠地继续,盯着我的脸说,“你随随便便,可能一周就出五天,那四十万是有的。最低哈。还有每个客人给你的小费,那都是你自己的。加起来十万二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是有可能的,看你自己。”
— 下篇明日发布 —
BIE别的女孩致力于呈现一切女性视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儿艺术家创作,为所有女性主义创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书写 HERstory。
我们相信智识,推崇创造,鼓励质疑,以独立的思考、先锋的态度与多元的性别观点,为每一位别的女孩带来灵感、智慧与勇气
公众号/微博/小红书:BIE别的女孩
BIE GIRLS is a sub-community of BIE Biede that covers gender-related content, aiming to explore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ales. Topics in this community range from self-grow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ender cognition, all the way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art. We believe in wisdom, advocate creativity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question reality. We work to bring inspiration, wisdom and courage to every BIE girl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a pioneering attitude and diversified views on gender.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