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政策、知识分子与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滕彪专访林培瑞
滕彪(以下简称滕):林培瑞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的访谈,也感谢您对这个刊物的支持。
林培瑞(以下简称林):很高兴。我很愿意支持季刊的工作。
滕:您经常批评和分析西方国家和知识分子在中国问题上的天真,那这些天真有哪些表现呢?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但是在政治上越来越专制,这个和西方的天真有没有什么关系?
林:这个问题有好几个层面,本来是很老的一个问题。欧洲的启蒙时代有一些羡慕儒家社会的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莱布尼兹(Leibniz)等,他们一直非常羡慕中国,把中国看成是一种神秘的、理想的不同文化,其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有。
一般美国人接触到中国人、中国的菜肴、书画等等,马上有好感。中国人友善、菜很好吃,中国文化是个很神秘的、应该尊敬的古老文化。近几年来尤其是我们政府里头,我觉得有一种对等主义,很多不懂中国的美国官员,看到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就推测这可能也是北京的运转方式。那当然不是,完全不是。可是他们不知道,所以把自己照镜子过去,以为中国大概跟我们的运作方式是差不多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美国人需要“看穿”。否则就不知道共产党从1940年代以来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掌控权力、要接管一切(take over)。“为人民服务”那些漂亮的口号都是工具,目标就是政治权力——党的权力,有时候甚至是个人的权力,比如毛泽东时期。美国人不知道共产党的这种性质,对历史缺乏了解,没有看穿。我说的这一大堆都是所谓“天真”的表现。
滕:您刚才说的“照镜子”式的对等主义思考模式,我也很有同感。我经常告诉学生要警惕“对应主义”(counterpart)思维模式,比如说西方有法院、法官,中国也有法院、法官。但是中国党国体制下的法院、法官,跟正常的法治国家的法院、法官,他们的地位、角色、功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类似的还有宪法、议会、政党、律师协会、选举等,如果把中国的同样概念所指代的事物想象成、理解成和欧美同样的东西,就会产生巨大偏差。
林:所以这种语言会误导那些天真的美国人、欧洲人,他们把语言看成是事实,甚至是自己照镜子的事实,那就离谱得厉害了。弄到最后比如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种看法的前提就是那种天真。共产党能够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吗?他根本对中共的性质缺乏了解。
滕:对。比如中国宪法、法律里有很多关于公民基本人权、基本自由的规定,中国也加入了很多旨在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条约,还有中共领导人的讲话、种种承诺,看起来都是非常漂亮、非常进步的,很多天真的人就会认为这些是共产党变好的迹象,或者以为共产党一定会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信守承诺。
林:而且应该指出,共产党之所以把这些漂亮的名词、规则推出来,就是因为它既能够欺骗外面的,也能欺骗自己的老百姓。我们也有言论自由,我们也有公平选举,如此等等。
滕:受到蒙骗的很多人中,可能就包括比尔·克林顿。他当总统时在批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就说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进入国际贸易,最后会发展出来一个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一定会要求民主,然后就会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政界、商业界和学术界的多数人都认可这种判断。后来最惠国待遇变成永久贸易伙伴国(PNTR),中国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种天真的乐观都普遍存在。
林:对。因为欧洲历史有这种潜力(中产阶级推动民主)是真的。这种天真的人是好心的,他们真的相信这种转折(经济自由导向政治自由)会在中国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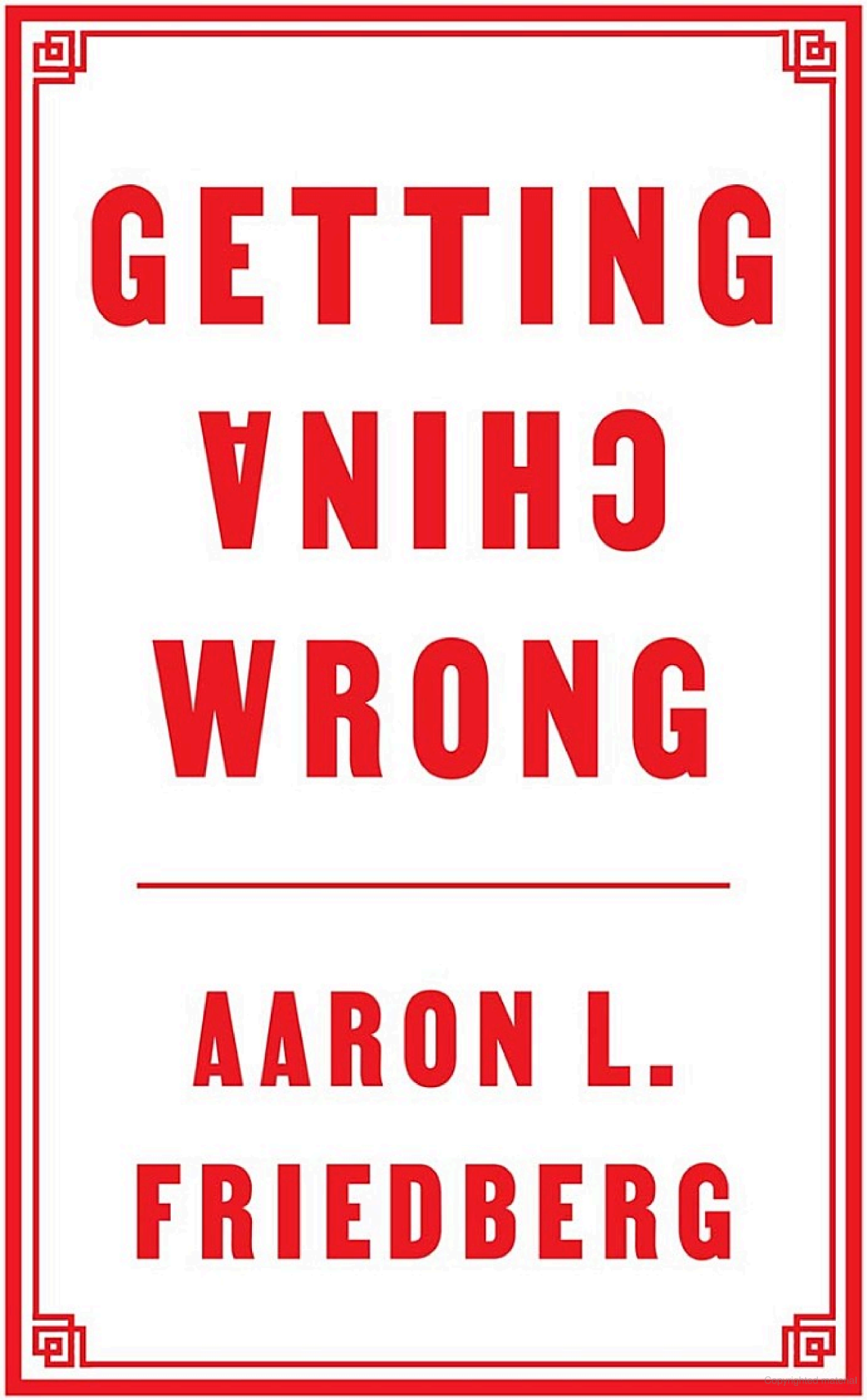
滕:普林斯顿大学的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叫《把中国弄错了》(Getting China Wrong),他说西方对中国发展的一个错误假设,就是和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推动中国走向开放和民主;西方也同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野心。孟捷慕(James Mann)早在2007年的《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一书中就分析了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一厢情愿,您是否同意他们的分析?
林:我当然同意。孟捷慕是我的老朋友,范亚伦是我当年在普大的同事。这两个人的书我都读过,很佩服。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道理当然如此了,What's new here?(但这有什么新鲜的呢?)他们的书是针对一般的美国政客,但是美国普通老百姓不知道这些。所以这两个人去分析西方人自己的天真的来源和毛病,贡献是很大的。但是他们的兴趣跟我个人的兴趣稍微不同。尤其是范亚伦(Friedberg),他担心中共在国际政治上采取扩张主义或一种挑衅好斗(aggressive)的姿态。台湾、南海、菲律宾、跟印度的边界等等,这我都知道,但是我个人关心的主要不是共产党的海外扩张和影响,而是在国内做的事情。共产党对中国人做了不能再坏的事情,比如大跃进、大屠杀,甚至把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心灵给严重扭曲了。现在从中国出来的年轻人,价值观扭曲得很厉害。也不能完全怪他们,他们就是那种教育和社会环境下长大的,信息资源受到严格限制。比如他们觉得在课堂上作弊无所谓,作弊不被捉住就是高手。这是从哪来的呢?这共产党毁坏了一代两代,甚至好几代中国人。我关心的是这些问题。
滕:犬儒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极为普遍,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不是特别确切,但是他的观察是准确的。人们没有基本的原则,完全为了自己自私的利益进行计算,缺少共情、缺少公共关怀,甚至随时准备做各种各样的坏事。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歧视农村人、穷人,歧视女性、性少数群体、残疾人、相貌不好的人,等等。一个人只要有了钱、有了权力,就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
林:我很欣赏钱理群教授的分析。而且最痛心的是,他们不觉得犬儒主义和不择手段是坏事,而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光荣的事、有本事的表现。这主要怪共产党,共产党那么多年的违背人性的教育、控制媒体等等,产生了这样的中国人。
滕:中国现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严,共产党的各种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加上犬儒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可能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有很坏的影响,对和中国有交往的其他的国家、对整个世界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林:这种病毒会蔓延的,我同意。
滕:谈到和中国的交往,从尼克松以来美国就实行一种接触、交往(engagement)政策,在2016年后,奥巴马任期的最后阶段、特朗普上台后,有关接触政策有比较多的争论,再后来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有了重大变化。在您看来,接触政策是不是已经失败了呢?哈佛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有篇文章《“接触政策失败论”的失败》(The Failures of the “Failure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大意是说,美国制定接触政策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包含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目标,那您觉得接触政策有这样的目标吗?如果美国对华政策并不包含推动中国民主的目标,那么应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呢?
林:江忆恩的分析,包括你的问题,属于国家对国家层面的接触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应不应该是接触(engagement),这当然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也能够看到老百姓之间的各种交往,学生,移民,做生意的,专家学者,等等。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很多,到中国去的美国人以前很多、近来在减少,所以人民对人民的接触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层面,甚至是比政府间的接触更重要的层面。最近“润”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很多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为什么呢?这些中国人感觉美国有吸引力。设想一下有多少美国人挤到中缅边界、闯进中国?没有。美国的自由社会还是有吸引力,不管美国的政府有什么毛病,不管共产党、小粉红如何骂美国、骂日本。……民间的交往不会断,而且对中国的进步会起到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滕: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接触,中国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并没有像最开始预期的那样,走向一个开放社会和民主,接触政策好像是失败了。但我认为,虽然现在的确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糟糕,也没有朝着民主方向在走,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在民间社会层面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比如说我作为维权律师在中国曾经非常活跃地推动维权运动,成百上千的律师利用法律来捍卫公民的权利,比如说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比如成百上千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成立,从事劳工、环境、教育等等方面的倡导,比如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像刘晓波、许志永、贺卫方这样的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接触政策的话,这些成绩都很难获得。
林:确实如此。刘晓波有一篇文章,讨论言论自由与网络的关系,他讲了六次地方官员滥用权力迫害民众的故事,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到中国来,受苦的民众就上网控诉,一上网,附近的老百姓就支持那些受害者,因为他们应该有言论自由,他们说的没错。刘晓波问,这些老百姓需要我去教导他们人权是什么、需要我的理论吗?不需要。人们应该有言论自由、有基本人权和尊严,这是天生的感觉,从自己的生活出来的一种自发的、本能的意识。刘晓波最后一本书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那种正义感,是非感,即使经历毛泽东、共产党的多年荼毒,也没有被消灭。知识分子应该帮他们用网络、向他们学习、跟他们合作。这种本来就有的共同价值观就是希望,我很同意。观察、研究中国政治,眼睛不能仅仅盯着中南海,要多多地看社会、看老百姓、看日常生活中的抗争者。
滕:刘晓波的有篇文章叫《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这也是他判决书里面列举他的几大罪状之一。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最大的、最优先的选项,就是维持他政权的稳定,是它的一党制。您觉得共产党的目标,是不是还包括向全世界输出专制模式、把全世界都变成专制政权?
林:毛泽东时期说全球的普罗(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这是空话,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习近平、中共的高层,真的关心非洲、南美洲老百姓的生活吗?不可能。它扩散到全球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好处、获取资源。说什么为了全球老百姓的好处,要弄出一个新的、适用于全人类的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不相信。这是宣传,共产党自己可能都不信。
滕:共产党的大外宣、对外渗透很厉害,包括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渗透和操控,近些年出来越来越多关于跨境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报告和研究,甚至发展到在境外骚扰、殴打乃至绑架异议人士。中共不一定有野心把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变成专制,但他们要确保国际环境、媒体舆论、国际格局能够有利于专制政权的存在。
林:对,是这个道理。
滕:如果接触政策不灵了或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不是要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遏制,或者和中国完全脱钩?
林:我得分析“中国”两个字的意思,一定得把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分开。我们应该对抗中共,早就应该对抗,不应该不对抗,应该继续对抗。这没问题。但是对中国老百姓呢?我们应该接触,应该互相了解,应该做朋友,应该支持民间组织。对中国的政策,我绝对要强调这个分别。
滕:我认为,和专制国家进行各种交往接触而不过问民主人权,就近似于绥靖政策(appeasement);我正在阅读一本书《有原则的接触》(Principled Engagement),我觉得对中国应该采取有原则的接触,接触应该以不违背人权和自由为原则。您可以从这里展开来谈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对美国、对中国、对全球很多事务都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问题上也引起不少争议。共产党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石宇(Isaac Stone Fish)在2022年《美国第二》一书里,把基辛格称作是中国影响的代理人。也有人批评说,在基辛格的脑子里,并没有把中国跟中共分开,因为中国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中共也会是永远存在的。您如何看待基辛格的对华政策和他的政治遗产?
林:我非常讨厌基辛格。从哪儿说起呢?他1972年到北京跟周恩来见面,他为了联合中共对付苏联,出卖了台湾,说只有一个中国,后来让共产党把这个话理解为唯一的中国是北京的中国。这个种子是基辛格种下的,而且起了非常长远的、不好的影响。他写了很厚的一本ON CHINA(《论中国》),自以为懂中国,其实他不懂。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他其实一窍不通。他可能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学了点中国历史的皮毛,但是他以为他跟周恩来见面就能够看出一个比较深刻的中国,这完全是骗自己、骗别人。
而且他也不是那么诚实。他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发大财。介绍中共的高级官员跟美国的大资本家挂钩,赚了大钱。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九一一”之后小布什总统想让基辛格参加“九一一委员会”,他拒绝参加。因为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要公布个人所有的有利益冲突的文件。基辛格事务所当时在中国赚钱很爽,他不想受影响。
滕:基辛格也被当作是拥抱熊猫派的一个代表,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华政策被分成屠龙派(Dragon Slayer)、熊猫拥抱派(Panda Hugger)、汉学派、外交派等,您觉得这些分法有没有道理?这种状况是不是正在发生变化呢?
林:我不反对这种好玩的标签,但是我不喜欢,我不用屠龙派(Dragon Slayer)、更不用熊猫拥抱派(Panda Hugger)这些说法。熊猫很可爱,我们都很自然地喜欢熊猫,把熊猫跟中共划等号是骗人的。共产党绝不是可爱的熊猫。熊猫大概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全可爱的动物,它也得生活;但是它绝对没有共产党那种邪恶的性质,所以这么叫对熊猫是不公正的。
滕:这又涉及到中国和中共要分开的问题。中国和中共的关系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但是首先不能够把作为国家或文化的中国,等同于中共政权和中国政府。如果因为熊猫可爱、因为中国的诗词书画、孔子庄子,而喜欢中共,就没道理。
您如何看待“有用的傻瓜”(useful idiots )——不少国际学者比如贝淡宁(Daniel Bell)、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沙伯力(Barry Sautman)等等,以各种方式为共产党唱赞歌。有些人甚至在维吾尔种族灭绝、天安门屠杀等事件上为中国政府辩护。为什么如此?他们会影响西方受众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吗?
林:十几年前,还会有一些人听他们的。但现在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可是还在坚持。我觉得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他们本来可能是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相信共产主义的那种为人民服务啊,人人平等之类,有相反的现实例子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我父亲也是这种人,所以我比较知道这种模式。他们是好心的,可是就不愿意承认理想和事实是有区别的。第二个原因呢,像Daniel Bell讲那些东西比较时髦、与众不同、容易出名,如果只说主流的观点,就没有创新、无法突出了。
滕:故作新奇、吸引眼球。哥伦比亚大学的杰佛瑞·萨克斯(Jeffery Sachs)教授,是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有一次我们在BBC的节目中进行辩论,当时美国的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去中国讨论环境问题,我们争论的题目是要不要提出人权议题,我说当然要。杰佛瑞·萨克斯说,看看美国对印第安人做的事,看看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所以美国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中国人权、对新疆说三道四?我当场批评他说,这是一种特别粗暴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比烂主义”(whataboutism):“美国也做了很多坏事,每个国家都有人权问题,那凭什么揪住中国不放。”它能迷惑很多人。
林:这个立论的毛病是,它把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之间划个界限,说站在界限这边的人没有资格对界限那边的人有任何评论。这个完全站不住。我的隔壁邻居有人大喊杀人、抢劫,是不是我就不能过问别人家的事?当然不是,我们作为人类,对其他的人能够同情、能够帮助、能够设身处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而且不可能有。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难道因为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就不能为了别的国家说话了吗?要这样的话,普世人权就不可能有任何基础了。
滕:这就过渡到下一个问题。美国政治的这些年来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特朗普,他说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当选,他对中国的民主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林:特朗普的政策很难预测,这个有点危险。不过他第一次任期里,白宫请了博明(Matthew Pottinger)、余茂春这样能够看穿中共的顾问——当然,这不是特朗普自己做的。这一次他让卢比奥(Marco Rubio)去做国务卿,他自己是古巴人,容易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我在各地演讲批评共产党,也常常遇见美国听众问那种“比烂主义”(whataboutism)的问题,但我发现东欧的人就可以完全听进去,他们明白共产党。
滕:我们已经讨论了西方解读中国的困难、美国对华政策等,接下来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国内,请您谈谈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您和他们有很多交往,对方励之、刘晓波、刘宾雁有深入的研究和专著。能否讲一下,您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政治的什么特点,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什么特点?
林:中国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刘宾雁,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他知识非常广、对中国的社会非常了解、分析能力也非常强。方励之、刘晓波也是挺有意思的例子。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头,共产党的文化里头,有一种我叫“山头主义”的东西,我想爬到山顶上去,我说了算,我是一把手。这种“一把手主义”相当普遍。我不想说这句话,但是是真的,中国的异议人士、海外民主运动里头也有这种想法。而方励之没有这东西,因为他的政治理念是根据科学来的,科学里头没有一把手主义。平等精神、真理的普遍性也和科学有关。作为科学家的方励之很容易接受现代化的民主制度。
刘晓波年轻的时候也有点儿山头主义。可是不知道怎么,他在1990年代之后、尤其是1999年他坐了三年牢之后,认识他的朋友都说,他人变了,变得很谦虚,我想很可能是跟他在劳改营里阅读的、刘霞带给他的那么多书有关。谦虚、平等待人、尊敬别人的态度,在中国不能说是很普遍,所以我佩服这两个人。中国文化的山头主义、一把手主义,我们需要警惕。刘晓波也说,民主转型的一个关键,不是从上往下的宪法怎么写,而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彼此之间的态度问题。
滕:刘晓波2017年在监禁之中去世,中国政府对民间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打压,而且这种压制越来越恐怖。很多人被抓、被判刑、被禁言、监控也越来越严密,您觉得中国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推动民主转型还有空间吗?
林:民间的空间越来越少是真的。习近平以来就弄得越来越少,但是没有消灭它,也不可能消灭它。原因是我们刚才谈的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的价值观没有被毁灭,它有可能得到培育和发展。最近张彦(Ian Johnson)有一本书《星火》(Spark)。他讲到很多中国人,像林昭、遇罗克他们,从反右、文革的时候,到民主墙、到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到2000年代维权运动,一直到最近的白纸运动,你看一点一点的星火,每一次都被压制,但是没有彻底压死,都会再次回来的。原因是你我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和人性。共产党没办法消灭人性,星火就能够复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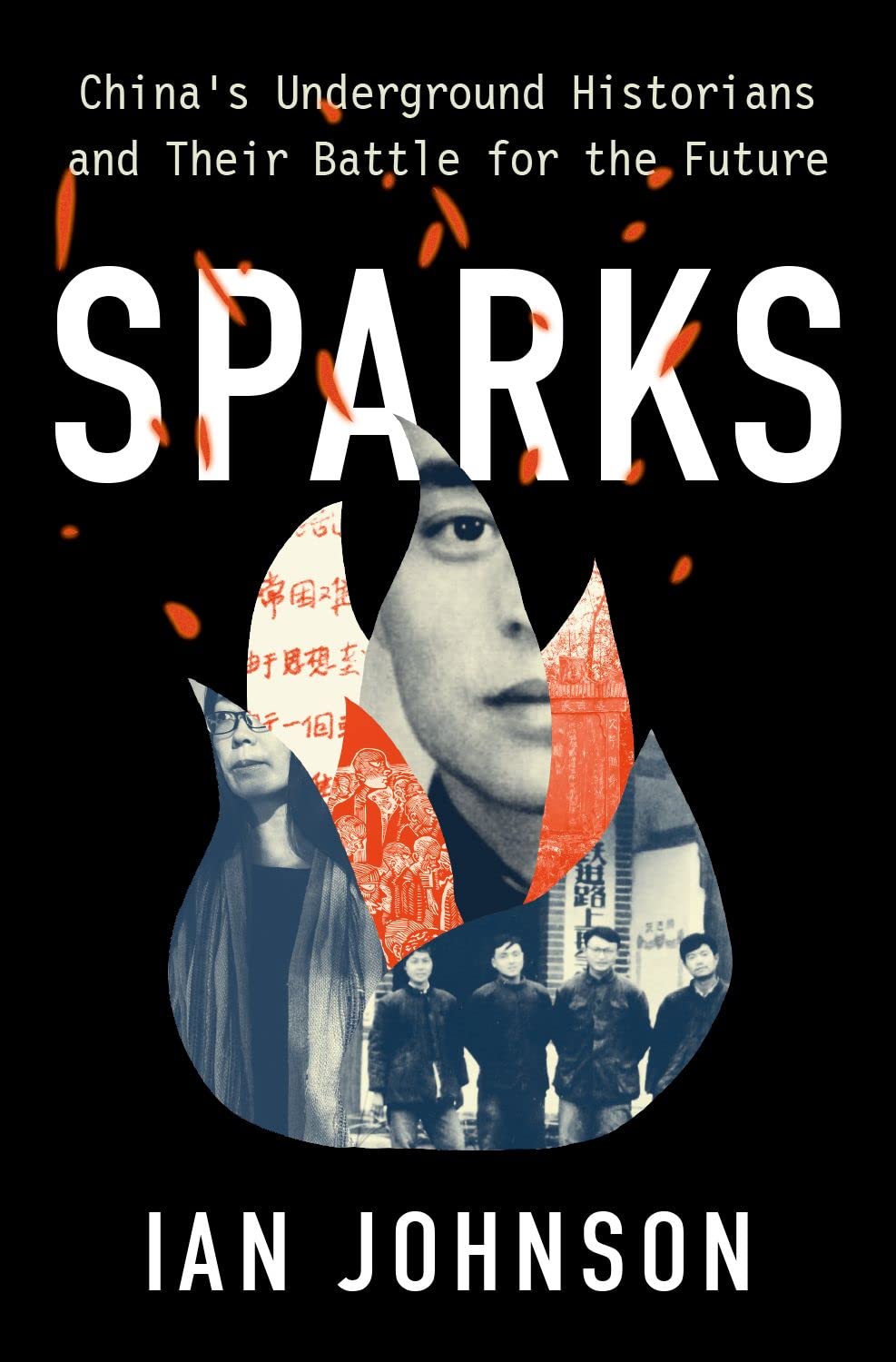
滕:张彦说他们是“地下历史学家”,在非常艰难的、危险的情况下,去书写历史、传承记忆,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林:他把这个跟中国传统的“义”和江湖文化连在一起。两千年来有不少冒着生命危险敢对皇帝说真话的人,屈原、司马迁、董狐直笔等等。当代传承星火的人也是继承这个传统。我们记日记、写文章的缘故之一,是要保留给将来,希望将来的中国人回顾习近平时代这样一个黑暗的年代,虽然黑暗但还是有人在坚持,没有死心。
滕:您有个有名的比喻“吊灯下的巨蟒”: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从而产生普遍的自我审查。这种情况是不是越来越糟糕了?
林:是变得更糟糕了。我那篇文章是2002年写的,对我来说是个比较新的发现。学界也觉得这提得不错,也开始注意。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知识,是常识了。“吊灯下的巨蟒”的效应很普遍。你挑战一个不正常的事儿,你想捍卫自己的自由,别人会觉得你不正常。我知道的一些异议人士,他们站出来说话,先是他们的家人反对。你愚蠢吗?你自己冒险,也让全家人都不安全?你怎么发疯了?因为灯下巨蟒的影响,不正常的就变成了一种正常的东西。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滕: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信息控制、强制遗忘、宣传洗脑对塑造民众的思想是有效的吗?共产党现在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来进行宣传洗脑和信息控制,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是不是越来越难以出现了?美国(乃至全球)互联网上大量存在的虚假和错误信息(disinformation and misinformation),对塑造人们的观点,包括影响选民的投票,都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您觉得这种虚假信息和中国的信息控制和言论审查能不能进行比较呢?
林:共产党的强制遗忘、洗脑有没有效?是有效。比如到我们加州来念书的中国本科生,常常都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到我办公室来问我说,六四的时候,到底是士兵杀学生多,还是学生杀士兵多?他在课堂里不敢问这个问题。所以洗脑是有效的。怎么对付这个现象呢?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揭露它的谎言,一个个地揭穿。让老百姓知道有假消息、有谎言、有洗脑宣传和政治操控。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或者全球的网络上的虚假信息越来越多,这是个应该严重关注的问题,要有意地揭露谎言、努力去反驳种种阴谋论。但是中共的假新闻和互联网上的假新闻有个很大的不同,中共假新闻是一元的、统一的,而外网上的假消息是分散的、多元的,你可以比较、有可能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滕:现在的中共不仅仅是沿袭传统的管控媒体、控制民间社会、洗脑宣传,而且它越来越多的采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包括智能摄像、人脸识别、大数据、各种人工智能等等,对社会、对每一个公民进行实时的、全面的监控。你有什么样的爱好,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跟什么人见面,它都了如指掌。是不是共产党可以借助高科技而持续维持其专制统治呢?
林: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我们不知道答案。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描写的就是现在这种局面,甚至连奥威尔都没有想到技术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利用大数据、算法(Algorithm)这些东西的,不只是共产党,其他政府、大公司也有这种东西。我不懂高科技的前沿,但高科技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对我来说,这是个有趣的、跟人性有关的问题。本来人是喜欢独立、自由的,不希望被观察、被监视,而现在的科技,电脑、手机、算法,让你不感觉到被监视。技术会不会跟人性碰撞?碰撞会怎么样?不碰撞可能更可怕,难道将来的人性能够习惯于24小时一直被观察?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个对根本人性的挑战的问题。
滕:您说人有追求自由尊严的本性,我很认同;但是日常生活无法摆脱的、无所不在的高科技和算法,会不会使得人性被重新塑造、被深刻地改变?新的人性是否更倾向于形成专制极权制度的温床?这是很前沿的深奥的问题。答案可能要留给我们的读者自己去思考。
林:是,我们大家要努力去对付。至于能不能,目前不知道。
滕: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回答。
林:谢谢你。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