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 “两头婚”的实景与幻象
近日关于浙江乡村“两头婚”制度的讨论因这一婚姻实践形式上的新颖激起了法律、性别、经济发展、姓氏观念等方面的讨论。研究者赵春兰2019年曾提到费孝通于193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已经注意到了“两头挂花幡”的两头婚实践。她认为“两头婚育模式则连接了传统伦理和现代价值,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当下婚育中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张力”。与这一略带功能主义的看法不同,本文作者梳理了两头婚制度的经济制度构思和实践上的困难,捕捉到了动态中的实景与幻想。两头婚绝非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也不是替代裹绕在社会关系里个人权责的制度。在结尾,作者回归到爱情德性论的视角。值得继续追问的则是,这一德性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框架如何使之可能,爱这一永恒的话题又如何在爱情德性论发轫的十八世纪英国、费老写作的民国江村、和今日的浙江农村这些情景中摩擦和嬗变。
作者 / 沈雪晨
编者 / 曾毓坤
近日,江浙一带日益流行的“两头婚”登上热搜。其实这个名词并不完全妥当,从字面看仿佛一个人在两头都有了婚姻,犯了重婚或在进行开放式关系(open relationship)。在现实中,江浙人只用吴方言将此唤作“不进不出”、“两家头拼拼”或“横平婚”。随后的报道和评论从经济社会的大背景出发,粗略谈及“两头婚”的形式与内容,以此论其优劣。这激发起恪守传统婚嫁形式地区读者的好奇心,却如同这个名词本身一样造成了许多误解。本文通过采访几位“不进不出”婚姻的亲历者,从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呈现两头婚的实景与幻象,结合Cohen、Wolf、闫云翔等对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探寻我们在追求幸福道路上的困境与出路。
01.
从共同经济到“不进不出”
举行婚礼前,小周其实没少和男友讨论未来的家庭生活:
“我想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你的反正还没装修,又远。”
“我户口,能不能别从我爸妈那儿迁过来,现在农村户口福利挺好的。”
“孩子养两个的话,一个姓你,一个姓我,好吧?最好第一个生出来的姓我,我爸年纪大了,挺想要个孙子的。”
“这样你其实比较划算的,我跟你讲啊,又有人给你生两个小孩,又不要出彩礼,现在讨个老婆很贵的!”
面对小周的连环炮,男友面露难色,但女方想的都比自己周全,说起来还头头是道。虽然觉得怪怪的,但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为了结这个婚,他还是从了。

小周的情况并非孤例,身边的小姐妹们,工作几年以后都自己买房了,父母还有几套房,自己每个月有稳定收入——婚是要结的,但嫁人就得看真爱和诚意了。身边优秀的男孩子,早就“名花有主”了,要找到合适的伴侣,还得多请朋友介绍、父母安排相亲。
小周的婚礼如期举行,亲友群聚而来,对于“不进不出”这件事,并不以为新奇。司仪的吆喝伴随着餐桌上的饕餮,大家像平常一样聊着往哪里的房市板块看涨、谁家的儿子考上名牌学校,拿了烟酒糖果,各自回去生活,小富即安。小周很快怀孕了,两个家庭静静等待着新生儿出世,而第一个孩子的姓氏,则按照规划给了女方家庭。
若要问起江浙人对“不进不出”的定义,答案在相当程度上是明确的:男方不出彩礼,女方不给嫁妆,婚前约定生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姓女方。小周的案例稍稍特殊之处在于,通常情况下第一个孩子是姓男方的,且为了显示公允、避免计较,在理想上,孩子不论男女,都按照婚前约定的姓氏来取名。与小周夫妇在开头的对话不同,正式的谈判都会由双方父母出面,分配姓氏不论男女、只讲先后谈法比较客气礼让,不容易破局。从几位采访者中得知,提出“不进不出”需求的,通常是女方家长,因男方会自然倾向于“讨老婆”的传统形态。我们还可以为这样的女方家长做一幅素描:重视自己家的姓氏传承,不希望因为女儿出嫁就门下无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通常与男方家庭相等甚至略胜一筹。另外他们中有些有农村背景,有些是拆迁户。这些标签化形象未必能反应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却能让我们用最短时间了解这一群体的面貌。
在有关中国家庭制度与生活的民族志(Ethnography)书写中,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模型是所谓“合作社模式”(the corporate model),其中的中国家庭被视为由完全理性的、明白自己利益所在的成员组成的经济实体,它包含财产、经济、群体三个要素(Cohen, 1976),能够具有弹性地调动家庭内部的人力物力,利用外部机会,为整个家庭共同的财产和收支计划谋福利。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经济单位中,财产共有制是制约每个成员的主要途径,他们间的合作亦是以共同经济利益为导向的(e. g., Fei, 1946; Cohen 1970, 1976; Baker, 1979)。
很显然,在“不进不出”的新形态家庭中,财产的共有制很大程度上难以维持。以往江浙地区的彩礼和嫁妆通常是留给新婚小夫妻建设新家庭的,不出彩礼、不给嫁妆,小夫妻们就失去了婚后第一座共有小金库;以往房子和车子由男方置办好,媳妇取回来这些名义上就成为两个人的共有资产,而现在男方女方各自有房了,即便结了婚,财产也还是自己的,你不占有我,我不占有你,身体在一起,财务依然泾渭分明;以往孩子随父姓(在招女婿的情况下随母姓),现在一边一个姓,孩子成长所需的财务分别由两个家庭分摊,传统上因抚养子女而进一步巩固的共有制也被瓦解了。在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 Wolf)针对中国台湾农村妇女的研究中,曾补充性地指出中国家庭并非一个和谐的整体,妇女可以在家庭内部利用各种资源,努力争取自己权益,形成“家内有家”的形态(Wolf, 1972)。而江浙一带采行的“不进不出”,则给家庭成员纯粹为自己谋利提供了一个高度正当化的办法——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即便结婚了,我也只对自己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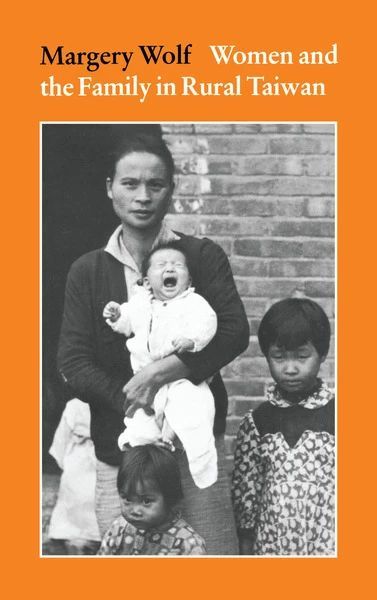
这将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在访谈者中,颇感婚姻不幸的小余就这样自述:“当我花我老公钱的时候,他总觉得我花的是他的命!”——看来这位先生已经具有坚强的婚内财产私有观念。然而情况又不只是如此,小余说:“那我花我自己钱总行了吧?他连我花自己的钱也要管,甚至连我父母的钱,只要存着不花,他都觉得是他的钱。”——看来这位先生又悄悄把太太的钱“共有”了起来。小余或许未必明白里面的问题出在了哪儿,她试图使用丈夫的财产失败了,想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又遭遇阻拦,最后她只能把问题归结到:“我们三观不同,钱挣了不就是用来花的吗?”
02.
两头以外的线头:扩大家庭与亲密关系
除了共有经济实体遭遇挑战,小余的困扰还包含着传统家庭间性别与代际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所面临的新情况(Greenhalgh, 1994)。以往由父权、夫权主导的家庭秩序,现在又加入了老丈人的权力、丈母娘的权力,他们可不会像以前那样听之任之,用一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现在两家是平等的,凭什么公公婆婆说了算?一场全新的家庭权力博弈由此展开。小余自述道:“目前的不满意,另一方面是来自对老人,两个小孩会被区分成你们家的、我们家的,时间久了,双方家庭多多少少有些矛盾——一开始大家都会稍微让一让,可毕竟一直让是不可能的。”
这里之所以先不提太太的权力,其实是另有诠释空间。从表面上看,女权通过这种新形态的婚姻,在名实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确保。但千万不要以为藉此就能回到母系社会了,即便其中一个小孩姓了女方家庭的姓氏,此姓的来源仍然是男人——一位热心提倡“不进不出”婚姻的老丈人。真正属于太太的权力呢?以往嫁娶形态里那种对先生的灵活权威不见了,“小鸟依人”也不行,“母老虎发威”也不行,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谈,先生又有种权威失落的遗憾情绪。即便再把老丈人搬出来也没用,现在不比婚前,谈判起来,两家人不容易那么客气了。在这方面碰到的难题,甚至会让“不进不出”的丈夫觉得自己当初不如直接招女婿算了,这样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难道就是当初选择不慎?
倘若我们抛弃结构与制度的冰冷框架,不谈论财产和权力的现实问题,转而深入到亲密关系、情感体验的私人生活内部(Yan,2003),情况又是如何?小费家原本是城市周边的农民,拆迁以后,拿到了一笔补贴和一间大房子。结婚时,他们已经不在乎男方家庭给不给彩礼,无所谓嫁娶了。两家按“不进不出”的办法商量好,生两个小孩各自姓。计划赶不上变化,先生婚后常常因公出差,公公婆婆在带小孩方面又不够细致有耐心,一个孩子生完,小费得了产后忧郁症,孩子虽然姓了男方,全由小费和自己父母带——“我应该不会想要再生小孩了,那段时间老公不在身边,我确实挺难的,看着父母这么辛苦,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再生一个不过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应当注意到,“不进不出”提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婚姻育儿模型,但在实践中却容易遭遇变数和复杂的现实问题,女性作为生育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在给予更多承诺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风险,其中产生的情绪和精神负担,往往需要自己承受。先生也未必不想体贴入微,但对太太来说,跟一个常常忙着工作、连自己吃饭睡觉都照顾不好的男人袒露产后心理问题,则需面临鸡同鸭讲的情形。

女性在“不进不出”的婚姻中还会遇到种种复杂情感。受访者普遍说,当初做这个决定,是“不想要离开家,不想要离开父母”,背后是觉得自己的家庭挺好的,过习惯了,为什么生活条件那么好,却要去别人家受委屈。随后她们会产生一种“即便结婚了,也没有嫁出去的感觉”,这种情绪十分复杂,在正向积极时会凸显女性的独立特质,但在感受负面或需要支持时,则会强化孤立无援之感。此外,“平等”的观念在这种类型的婚姻里是被先天确立的,但两个人的进步无法保持时刻同步,当其中一方(尤其是女性)的进步较大,有更长远的目标和更高的生活追求时,对先生的不满程度也会变得更多——前面提到因财务问题而颇感不幸的小余,同时也对先生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态度有所不满:“有些人觉得他自己现在很好了,比一般人都好了,就安逸现状,但是有些人,一直想往更好的地方去攀登!”为此,她感到很失望:“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不会选两头婚。”
03.
两头婚内的爱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幸福的家庭却个个相似。在受访者中,也有两组“不进不出”的典范夫妇。小青和先生都是独生子女,婚前没有特别谈这个问题,两家人颇有默契地做到了“不进不出”,不给对方增加财务负担。婚后小青先养了一个女儿,按规矩姓了男方;过几年又生了一个儿子,本该姓女方的,但是家里商量了一下,考虑到男方家里四代单传,好不容易有个男娃,女方就主动放弃了,姐姐弟弟都一个姓。现在两家不区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平时都是两个奶奶一起带娃,老人在一起彼此陪伴,孩子也不会孤单。偶尔会有些小摩擦、小矛盾,但是老人们为了孙子孙女,都很讲分寸,先生太太又会跑来当和事佬,因此问题不大。小青感慨说:“我知道有的家庭为了个姓闹得不愉快,这方面主要看家长,我们两家好弄。我跟我老公运气好,父母都为自己的孩子考虑,给台阶就下。”
小李中学毕业就离开了江浙,去深圳读大学,认识了现在的先生。结婚时,女方特意不要聘礼,“我爸妈不喜欢那种感觉,要了聘礼像是卖女儿哈哈”。结婚时,男方先在深圳买了房,两人先安家落户,随后女方家也筹划着在那里买房:“因为是第二套需要7成首付,我们还在看房,爸妈也不是因为对方买了才买的,纯粹是想把最好的给我。至于车子就更不用说了,老公一毕业就买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足以换好车了,不用家里买。至于姓谁,可能有些家庭比较在意,我父母不看重这种习俗。”小青和小李的家庭都显示出在经济事务上的开明,并提供了为对方妥协的空间和更强的共情能力,同时也很注重彼此间的沟通。亲属关系意味着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亲人内在于彼此的身份和存在之中(Sahlins,2013),两个家庭是否为两头婚做好了准备,并在过程中给予对方支持,影响到这段婚姻能否顺利度过难关。

英国十八世纪的女性主义哲学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曾说,我们必须根据理性、美德和知识的程度来衡量我们本性的完美以及幸福的能力。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婚姻形式,“不进不出”在经济制度、权力结构、情感体验等不同方面都向传统中国家庭提供了新方案,导致亲属关系内部发生变异和松动;当它将“男女平权”观念深植入这场婚约,其实对双方的德性和智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白这样的道理并非难事,难的是在纷繁杂乱的现实生活中,在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中,在光鲜亮丽的种种诱惑面前,不断实践和体认“平等对待,共同奋斗”的真正含义。情欲消退,热恋短暂,要找出使爱情恒久的秘密,需要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不放弃自我更新的努力。因为真正的幸福必须从适当节制的情感中产生,而情感是包含责任的(Wollstonecraft,1792)。
这也就是说,在两头婚的实景与幻象中,我们最终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仍是学会如何去爱。实际上,两全其美、谁也不吃亏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要避免两性关系在先天上和历史文化遗留中产生的不平等更非易事,婚姻中总有付出得更多的一方,双方的付出多少也总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以此才有相互扶持。婚姻必然伴随着两个人之间、两个家庭之间的奉献和牺牲,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方能感受到爱和被爱。
参考文献: Mary Wollstonecraft,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 By Carol H. Post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Myron L. Cohen,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 the Chinses Domestic Group.” In Maurice Freedman ed.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pp. 21-3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Hugh Baker,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usan Greenhalgh, “De-Orentalizing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merican Ethnologist 21 (4): 746-775, 1994. 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shall Sahlins, What Kinship Is And Is Not,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费孝通:《生育制度》,收录于《费孝通全集》第四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382页。 孙中兴:《爱情社会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email protected]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读书会第30期 |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 Corona读书会第7期 | 全球公卫中的跨国人道主义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夏季
- Corona读书会第28期 | 大坝与水利政治
- 特朗普人类学(一):手、谎言、#魔法抵抗
- Graeber丨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 黑色海娜:对苯二胺、孔雀与不存在的身体
- Corona读书会第32期 | 松茸的时日
- 编辑手记 | 《末日松茸》: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
- 影视造梦:横店“路人甲”们的生活群像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小丑”
- 哀恸的哲学:“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11-12月
- 从丁真到拉姆:直播时代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
-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基督教,和圣诞节
- 结绳志的二零二零
- “两头婚”的实景与幻象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