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沉没的纸船:当代偶像剧的厌女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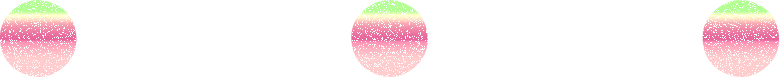
成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某一侧面,国产剧终于出现了诸如《风吹半夏》《欢乐颂》《二十不惑》《爱很美味》《亲爱的小孩》为代表的、探索现代女性生存状态的作品。然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试图摧毁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再一次地被捕获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下:资本对于外部的吞噬是贪婪而无立场的。和好莱坞将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社会边缘群体扭曲地编排在被层层包装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清教文化之中一样,中国的“女性话题”同样扭曲地、同样“令人欣喜地”强塞在从未改变的集体厌女和庸俗社会哲学中。
面对一系列以女性意识、女性权利、女性生存现状为创作核心——不论是否只是幌子——的作品,我在充满敬意、摇旗吶喊之时不由得心生怀疑:我们是否此刻正坐在一艘注定沉没的纸船之上,却已经不合时宜想象着涉渡苦海之后的未来。女性的苦海中的每一滴水浸透着血污、汗水、精液和眼泪,我想,一艘这么脆弱的纸船恐怕承载不了这么多人、涉渡过这么辽阔的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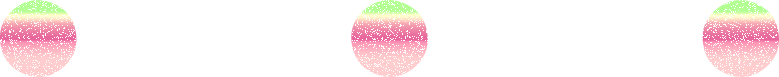

如果说好莱坞电影工业通过营造幻梦而安置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偶像剧制作工业构建的梦幻舞台所安置的对象显然明晰许多:年轻的帅哥美女们的粉红色爱情。不对,如果仅仅将偶像剧定义为“粉红色的梦幻恋爱”显然是一种偏见。只是,至少针对这几年的国产偶像剧而言,不论是创作者还是粉丝观众都乐于接受这种偏见。
近年来的偶像剧市场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传统的叙述方式开始失效:不论是《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等二十一世纪初的韩剧模式,还是《公主小妹》《命中注定我爱你》之类的台湾偶像剧套路,或者是以匪我思存、顾漫、丁墨、唐七公子等等网络写手为代表的“晋江文学”改编潮流都在偶像剧的自我革新中淘汰——更不要说更早古的琼瑶式苦情戏了。
偶像剧的自我革新当然内在于东亚三国的女性意识觉醒过程,这同样是个相当有趣的议题:中日韩三国偶像剧的演变过程和主旨倾向或许可以作为一处小孔,窥视到东亚三国都市社会层面女性意识发展的异同。
只是这种自我革新并不彻底,古早偶像剧的幽灵还附身在如今的偶像剧制作从业者的背后。那是男人的幽灵——这么说不完全对,那是幻想的完美男人的幽灵,是从冥界返程的阿多尼斯,是委身于父权制的创作者自慰时的幻觉。近期偶像剧中的《梦华录》中的顾千帆、《芳心荡漾》中的林森、《爱的二八定律》中的阳华(说真的,这个名字本身似乎就有某种弗洛伊德倾向)、《卿卿日常》中的尹峥等等人物应该可以作为典型(事实上可以列举的角色数量是相关偶像剧数量的数倍之多)。

这就是偶像剧的甜蜜陷阱:被幽灵附身的、倾倒于阿多尼斯的创作者制作的作品不论深入到现实地表的何处,都会散发着一股尸臭,不论它本身的香味多么浓郁。这是又一处艳若桃花、美若醴酪的红肿溃烂:恋爱,事实上不会是裹着糖浆的粉红色爱心饼干,这一过程始终是与一个具体的对象、与自我的幻想的角斗,是剑与花枝的轮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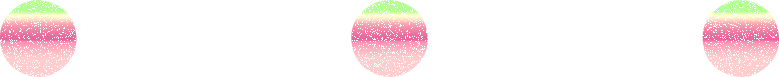

借用一个完美男性形象来实现女性的自我救赎,这是多么可怕的认知。然而偶像剧内在法则先天地要求这个完美男性在场的必然性,即:这注定是拥有美丽外表和高贵品格的帅哥美女的粉红色罗曼史。僭越这条法则的创作者大概会被偶像剧最重要的受众——粉丝观众审判且放逐于市场之外。
偶像剧的偏见——或者种偶像剧的内在法则对于出演偶像剧的艺人、及其粉丝是如此重要:粉丝得到了自我遮蔽的合法权,剧作中艺人以外的所有元素都被扁平为景片,而艺人则可以如同没有自我意识的芭比娃娃一样满足粉丝们的“换装”欲望。不,应该说只有自我遮蔽、并且将艺人视为没有意识的人偶才行,这样才可以将欲望放置其中,这是粉丝的“皮格马里翁情节”。在这里,粉丝们陷入了多么经典的拉康情境之中:她/他们欲望的对象始终是他们的欲望。
欲望、欲望的欲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欲望阻断了可能性。在这样的欲望之中,女性主义也被扁平为符号。完美男性、或者说偶像剧阿多尼斯一旦存在,女性题材作品都只会沦为可笑的“春梦”。
这些偶像剧中莫名其妙高呼“男女平等”、“姐姐妹妹站起来”的情节总是让我错愕,因为这是从来不伴随着斗争的“标语”。就像是《卿卿日常》里李薇和她的姐妹们那些越是正气凛然就越是可笑的宣言:关于自由恋爱、关于平等社会(去无视这部作品中那个虚构出来的女尊男卑的城邦和女主角那自由恋爱且一夫一妻制的故乡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不同男性对决、不改变男性,就永远无法实现“男女平等”。这种天真的情节应该只有“不想与男性为敌的女性”或者“谄媚男性的女性”以及“仅仅表面上尊重女性的男性”才会支持吧。

上野认为避免与男性敌对的女性主义者女性都是“冒牌货”,而为了避免与女性对决而无视女权主义问题的男性都是“反女性主义者”;那么在偶像剧创作这一情境里,可以宣告:创造出完美男性的偶像剧(尤其标榜自己是“女性题材作品”的偶像剧)都是彻头彻尾的冒牌货和反女性主义者。这多么符合厌女症的定义:男性的女性蔑视,以及女性的自我厌恶。因为完美男性-阿多尼斯的存在从来都不是女凝的产物:神话之中,阿多尼斯是父的私生子;而在偶像剧里,阿多尼斯诞生在异性恋霸权和景观社会的交媾之后。
如果不摧毁偶像剧的内在法则,如果不放弃欲望和幻想,女性题材的偶像剧永远都只能是致幻剂。

回到标题所提及的三部作品,最令我愤怒的是《点燃我,温暖你》,这部早古晋江小说改编电视剧的女主角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患有厌女症的女性。不,准确地说在整个故事中作为“地母”或曰奉献者、圣女面目出现的朱韵都没有完成自我的主体构建,这个女性形象是破碎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她只不过是李峋这个角色形象的填充物。我一直在思考朱韵这个角色来自于何处,直到剧情发展到她不惜抛开家庭也要和男主在一起之时,我终于意识到这居然是一个扭曲的“五四进步女青年”,一个“迷路的娜拉”。
朱韵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这个家庭是如此的“虚假的理想”以至于它仅仅只能作为“爱情的祭品”,是飞蛾扑火般的崇高爱情的祭坛。在这个故事中很难去分析朱韵的家庭异化,因为她既不是“母亲的女儿”,也不是“父亲的女儿”,她只是“李峋的女人”被镶嵌在了这个家庭之中。所以她始终是面目含混的,毕竟朱韵只需要作为那个“幽灵般的完美男人”的现实之锚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朱韵不过是文本内外的欲望媒介而已,只有这样观众才得以投射自我的欲望。

《爱的二八定律》和《芳心荡漾》《女士的法则》《我是真的爱你》等作品,也同样是背负着幽灵的创作,只不过所聚焦的话题现实意义更强。诸如女性职场歧视、职场性骚扰、职场女性婚姻及生育等等问题,在偶像剧中给出的灵丹妙药就是“和年下弟弟恋爱”。尤其是我发现《爱的二八定律》的男主名字是“阳华”,这一刻我似乎听到弗洛伊德的灵魂在我耳边咯咯大笑,我只能不快地别过脸去。如果说弗洛伊德是将人类所有的行为都解释为一种欲望的无意识运作,那么偶像剧则是将这种泛性论点缀成更加精美的甜品。
不过最让我不适的作品是《卿卿日常》,这种甚至不适感超过了《传闻中的陈芊芊》和《梦华录》。
《传闻中的陈芊芊》中那个所谓的“母权社会”不过就是“父权社会”最暴力、最没有想象力的性别置换;而在《卿卿日常》里“母权社会”就显得更加可笑了,展现丹川这个母权社会的细节是那么的低俗而刻意:以川渝地区的“耙耳朵”文化塑造成“类三从四德”的礼教制度,并且负载在“一妻多夫”的婚姻关系上。可是崇尚一夫一妻制度的女主为什么只是批判了新川的父权制而对丹川的暴力搬演的母权制熟视无睹呢?对于母权社会竭尽全力地想象也不过就是把母亲也视为暴力而压迫的父亲吗?黄蜀芹导演曾经说过,女性视角就是“打开新窗看风景”,但是在《卿卿日常》里,还是一样的、糟糕景色。

《梦华录》中的父权崇拜、性羞耻让这部“风月救风尘”的故事变成了“挥刀向更弱者”的故事,将赵盼儿塑造成“贞洁的风尘女子”,再明里暗里讽刺“卖身的妓女”——实在找不出更经典的厌女了,甚至这是来自于女性视角的,对于“圣女”和“娼妓”的分离支配。但是《梦华录》所造成的不适感仅仅只是对于原著精神的背叛,看着编剧和导演此地无银的尴尬辩解倒是让我很开心:像看到装模作样的坏家伙一不留神露出马脚时他脸上根本挂不住的笑容一样令人开心。

而在《卿卿日常》中,剧作在塑造了“幽灵般的完美男人”之后,还塑造了“完美的、纯洁的、仅仅作为象征的正妻”,以继续稳定男主和女主的“自由恋爱”和“性纯洁”。我们知道男性的厌女来自于他必须通过对于女性(他者、非人者)的蔑视(异化)才可以自我确认,以成为性的主题而完满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但是厌女存在着悖论存在,即母亲;所以产生了“圣女”和“娼妓”的分离支配,即被限于生殖的异化(母亲、妻子)和被限于快乐(当然是对于男性而言的快乐)的异化(妓女、情人)。
也就是说,《卿卿日常》中的元英甚至是被隔离了生殖的正妻,于是她的欲望指向只能落在女主李薇身上,最终她成为了“同性恋的花木兰”。诸如郝葭、上官婧等角色也同样牵强,只是高悬的“标语”下面的人形立牌而已。
古偶给我带来最大的错位感在何处?正是一夫一妻制和自由恋爱。必须要再重复: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和自由恋爱全部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产物,或者说,近代的产物。以现代观众为对象的古装偶像剧不得不将现代文明的种种塞入前现代的壳中,这不可避免,何况真正重要的也是始终是“讲述故事的时代”。
古偶当然可以是童话,可以去虚构种种幻想和美妙。但是童话的美妙之处不在于童话世界本身的美妙,而在于情感的美妙。《白雪公主》《海的女儿》《长发公主》中的世界都如此残忍,就不用说《买火车的小女孩》或者《风之又三郎》之类的作品。可是古偶作品将其作品的舞台搭建得太过于含情脉脉,这种温柔也可以说是亵渎,毕竟阵阵哭泣的也不过是前现代女性倒挂在历史天幕上的漫野亡灵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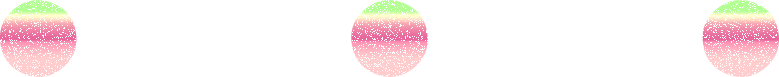

本来选择《点燃我,温暖你》《卿卿日常》《爱的二八定律》这三部作品是因为正好可以从恋爱关系、社会制度、女性职场三个部分作为基础去论述偶像剧的厌女症,甚至是中国社会的厌女症。但是很可惜的是剧作本身甚至连最基本可以展开论述的基础都没有,我所看见的就是那无限大的“完美男人的幽灵”。而且最让我矛盾的就是,哪怕在这样糟糕的作品之中,我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了张婧仪、田曦薇和杨幂的魅力。
上野老师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其实不仅仅是日本,也不仅仅是东亚三国,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都似乎将要从零开始。

我坚信女性问题依旧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才不知深浅地写下这篇文章:很浅薄地、很啰唆地、很肤浅地去分析了近期国产偶像剧中的厌女症。被偶像剧扭曲地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使我不安,尤其是在这个女性主义必需要从零开始的时代。
我们消费着这种文化,享受着这种文化提供的情绪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情感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在这样的文化之上被建构。我不想多言偶像剧文化对于中国视界、中国社会的结构影响,显然它以一种强有力地方式在塑造中国都市年轻一代的人际关系向往和恋爱、生育、婚姻思考,而且不仅仅是这些。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所有被我浪费时间的读者。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战战兢兢地思考中国女性的未来——不管这是否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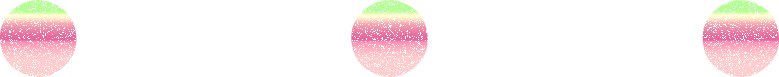
参考文献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 (法)米歇尔·福柯著. 佘碧平译.《性经验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 郭劼译.《消解性别》[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5. (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6. (日)上野千鹤子著.吕灵芝译.《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7. 周夏.《拯救与困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悲剧 1905-194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21
8. (日)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著.曹逸冰译.《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M].北京:新星出版社,202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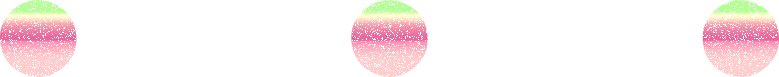

编辑:阿咸、泼泼
排版:人工智熊
Kongfu Girls是全网首个专注于服务女性影迷与艺术爱好者的文化社群。基于对当下流行影视作品的批评,我们致力于同女性观众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能抵御银幕歧视、纠正文化偏⻅的评价体系。
我们提供去中心化的讨论平台,组织写作活动和电子读物,以提高女性影人及其作品的可⻅度、提升女性在 评论界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我们鼓励女性发表自己的声音,分享真实的遭遇,在这里找到情感的共同体。我们要让被动的观看转化为主动的创造。我们要让女性与生俱来的勇气成为立场,要让行动与变革的信心诉诸文字。因为,每位女性读者和观众都是改善我们文化环境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公众号:Kongfu Girls
微博:她们的武术俱乐部
合作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