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二)
雜亂的異想還在太陽下醞釀著,一路上沒來得及孵出個意外,她已隨母親走到了掛號台。
「遲了十五分了。」母親叨唸著,不住向內張望,一邊捏著健保卡四處找著醫護人員。掛號處空盪盪地,一個人影也不見。櫃檯「初診」、「二診」的標示紙,紅紅綠綠地撩人眼目,泛黃的塑膠墊子上滿滿的黑色塗鴉,讓人相信這真是精神科門診。
「王曉帆!」護士打開診間的門,大聲叫道。媽媽拉著她走進了診療室。
醫生抬頭看了看曉帆,一面端詳著病歷。「怎麼了?」醫生轉著筆, 一邊問。
她沒有作聲。媽媽後面接了話:
「她心情不好啦,常常會哭。上禮拜在手腕上割了好幾道口子,被我痛罵一頓!
問她怎麼了,什麼也不肯說。」
「你怎麼了呢?」醫生問。
曉帆話還沒說出口,眼眶就濕了。醫生抽了一張衛生纸給她。
「這樣多久了?」醫生抬頭問媽媽。
「喔,好一陣子了,斷斷續續。本來以為是功課壓力大,我就叫她放輕鬆。結果
現在大考完了,她還是一樣,常常會哭。」
「這樣好了,我先開藥給她吃。」醫生轉向電腦,背對著她,一面答答地按著滑鼠。
「一定要吃藥嗎?」曉帆不耐煩地問。
「你情緒比較低落,吃藥會讓你感覺好一點。」醫生沒有回頭,繼續點選著螢幕上的選項,那已經稀疏的後腦杓,像張木然的臉。
「醫生,請問這是什麼原因?是本身體質還是環境造成的?」母親著急地問。
醫生轉過身來,在病歷上做了註記。「都有,我幫你安排心理諮商。一個月以後再回診,大概要持續個半年以上。」醫生半閉著眼說,像一句練到熟爛的台詞,隨手把病歷交給了護士,一面吩咐道:「叫下一個進來。」
那是曉帆第一次覺得,自己只是個號碼,螢幕一跳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曉帆推開諮商室厚重的門,只見眼前一片全然的白,整個房間靜悄悄地,連呼吸也變得勻勻淨淨地。諮商師拉開椅子招呼她坐下之後,自己就陷入了黑色皮椅的懷抱。
「說說看,你的感覺如何?」諮商師瞪大眼睛,看著她。
「我有時候很高興,有時候卻很悲傷。喔不,是常常心情很差。」她囁嚅地說。
「你低潮的次數太頻繁了,這樣很危險。」諮商師盯著曉帆講,「而且,你現在是一種受傷的狀況。這麼說好了,」諮商師挪了挪身子,接著說:「你的心目前是受傷的,就好比一個跌倒的人掉到井裡,旁人不經意的行為,很容易傷害到你,有點落井下石的味道。」
「而且,當你在低潮中走不出來的時候,很有可能會想不開。」諮商師翻到前頁的病歷,「尤其你之前有過這種行為。」被諮商師捏著的油墨紙角,像折了翼的幼鳥,空皺著一雙翅膀。「所以,你的境遇不是最悲慘的,卻會很難過。」諮商師仍望著病歷,看也不看曉帆。
如果感受是假的,那麼眼淚總是真的吧!萬蟻鑽心的痛楚與悲哀如此真實,不斷往心底竄,成了一個幽深的窟窿,這還不是最慘的狀況嗎?
「時間差不多了,你有什麼話想問我嗎?」諮商師看著錶趕時間似地,一面問道。 她閤上了病歷,往後靠著椅背,整個人頓時縮小了,像個小老太婆。
諮商師是不是都一直在看錶呢?曉帆心裡納悶。不然怎麼會如此準時?二十分鐘的諮商時間,總一分不差地結束。是啊,諮商師總是一面寫字,一面轉了轉手腕上的手錶。
「你們怎麼面對不喜歡的病人?」曉帆好奇地問。
諮商師清了清喉嚨緩緩地說:「這是專業的。我們受過專業的訓練,所以對病人有一定的忍耐度。」諮商師又瞄了一眼手錶,繼續說:「也就是本性不足的地方,我們會用專業去補足。」
曉帆突然感到很失望。原來她每一次訴說,還有聲淚俱下的一切,都只是就事論事,只是一份歸檔的病例。一想到這兒,她就寒心。諮商師的這層冷酷與漠然,讓她覺得診療時的坦白很耗神。
幾次診療之後,諮商師幫她安排了心理衡鑑,要鑑定她的心理狀況。
「啊!我們這次是要來看量表的,對不對?」諮商師雀躍地說,像要揭開什麼秘密一樣。她點了點頭,她很喜歡諮商師用「我們」這個字眼,承認她歸屬於某個團體,不再孤單。她要的就是這種陪伴。
諮商師一面翻開了量表,直接翻向封底數據,是心理傾向分析,上頭寫著:「患者是名內向的青少年,自我關切度高,有憂鬱傾向,挫折忍受度低。」
曉帆所有的感受,此刻都被粉碎成一個個無關緊要的數字,被加總、分析、曲解,被一種所謂「專業」的權威恣意地詮釋。
她覺得自己被肢解了,整個人被強行拆卸下來,照著專家的意思重組,拼湊成一個連自己也不認識的陌生人。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觀念?是我們心理學上常說的。」諮商師的雙手交叉握在膝上,身子向前傾了傾,問道:「每個人心裡頭都有一個小孩,需要大人去保護。不管外在的個人長得怎麼樣大,裡頭還是有這麼個小孩。不是懷孕的那種小孩。」諮商師的兩隻手撐在肚前,比了比大肚的模樣。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在你裡面,那個小孩怎麼了?」諮商師問。
「裡面那個小孩可能受傷了,累了……」曉帆感到有股力量直往鼻頭衝,她忍著接著說,「可是,她想自己站起來。」
「那她有辦法嗎?」諮商師挑著眉。
曉帆猶豫著沒有回答,只覺得自己搭建的城牆,被諮商師慢慢拆卸,她失去武裝的能力。
那晚曉帆做了個夢,磚瓦剝落了整個夢境。醒了卻只剩一身冷汗,什麼也記不得。她望著窗外青灰的天幕,只覺得渾身顫慄,恐懼感久久沒能褪去。
她不禁想起,上回她問過諮商師:「你們會被病人的情緒困擾嗎?」
諮商師搖搖頭,嚴正地對她說:「這是工作。所以下班後我就把它留在這裡。基本上你的痛苦還是在你身上,與我無關。」
「你的憂鬱症需要長期的治療、追蹤。」諮商師吩咐道,「我們定期聊聊吧。」
半年多來的診療,已經確定了病名。但她和諮商師終究是不相干的兩個人,就像合約裡的甲方、乙方,一切都是字面上的意思,沒其他情感。所有的日子只是曝光的底片。
也許一切歸零了,她就能重新開始。
三月的天空很晴,大片大片的雲彩,魚鱗一般遍布了天空,說不準什麼時候,魚尾一翻就落雨了,一股徹底的靜謐,隨著濕氣慢慢浸透她的鼻息。
她彷彿看到一頭憂鬱困獸遠去的身影,而心裏有一層什麼漸漸褪了——一層淺藍色的胎印。
#日曆#蔡牧希#游牧日曆#日子#手寫 #手寫文字#手寫語錄 #小說#小說創作#文學 #故事#poem#poetry#photo#photography #handwriting#病是迷霧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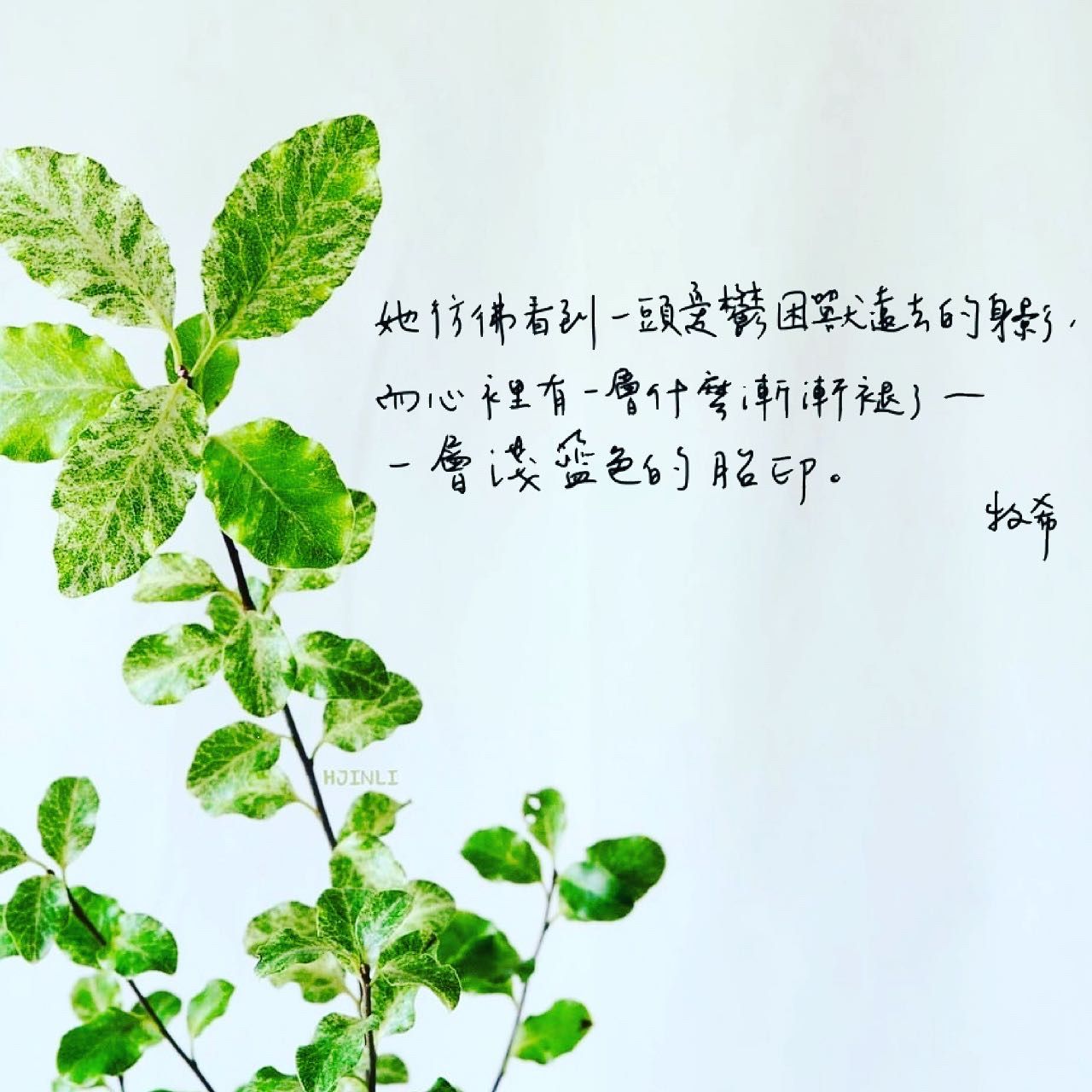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