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是我"故土的異鄉人",我亦是出走的娜拉 ——“德黑兰来信”回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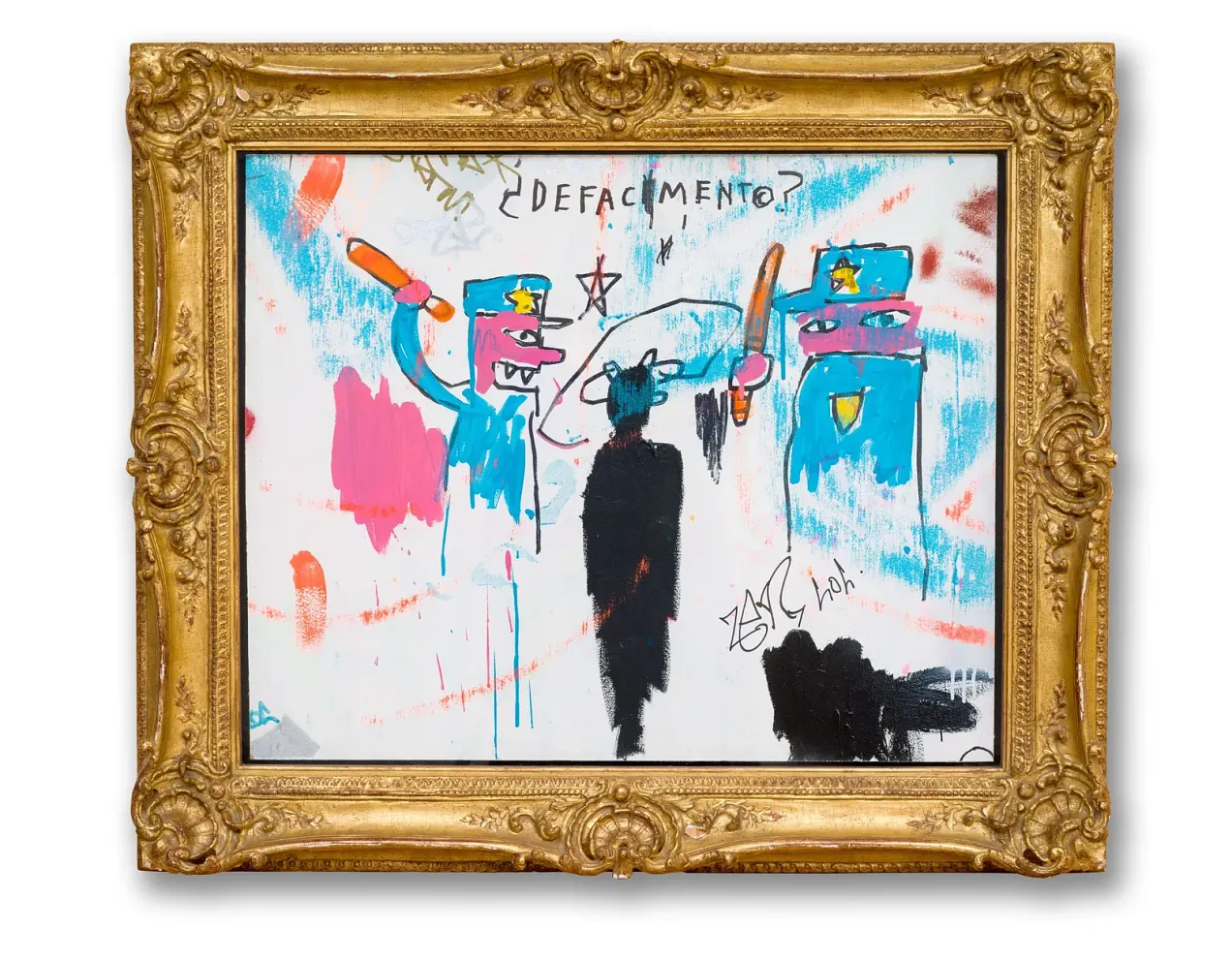
这是两则读者在“‘德黑兰来信’:中国被捕者家书”一文下留下的评论。事实上很多朋友提到,这篇文章让她们想起自己同样的经历。这让我们发现,那么多人曾经在万马齐喑中进行过力所能及的反抗,并且付出了生活被摧毁的极大代价。遭遇警察暴力在中国如此普遍,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听到她们的声音。
我们没有进行太多编辑,保留了评论者喜欢用的简体或繁体。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信,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应对警察暴力的经验或教训。我们的邮箱:[email protected] 。
经受过同样的对待,抓捕的时候我在家人的帮助下逃到了公园,把手机关机了依然能被追踪,幸好手机也丢了,最后出动了大量的警力警犬还沿路把车也拦了排查,幸好家人提前一步找到了我,害怕,现在看到监控就感到隐隐的害怕,即便在这里说话也感到害怕,万一起来以后就被警察抓了,总是忍不住这样想,对活着已经再无要求,对自己的命运也已经失去了改善的欲望,我能切身的感受到文章里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我心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淀(三个月),已改变了我,我无法确定这种恐惧给了我多大的影响,我只知道它已经彻底改变了我。
Mar 12
跟評論區與作者一樣,經歷過同樣的遭遇,同樣的對待,時間同樣是在十月。
我唯一幸運一些的地方,或許是我只被關了四天半。他們沒有找到我的私人手機,沒有證據,最後放了我。那段時間我正好在辦上一份工作的離職。原本順利的離職,因為這件事情被迫搞砸。那四天給我帶來的恐懼與創傷,是哪怕事隔數月,哪怕疫情政策早已轉向,如今的我都仍然無法向任何人完全訴說清楚的。
那四天沒有人知道我被帶走,沒有人知道我去了哪裡,在裡面的我也不知道還要被他們那樣折磨多久。他們二十四小時地突擊審訊我,對我進行睡眠剝奪,無所不用其極地威脅、恐嚇我。要我交代我的同伴,支持我的「境外勢力」,我過往在異地(HK, XJ)的經歷,以及拷問我女權主義者的身份。
我在被放出來後,抑鬱直接復發,生活秩序被完全摧毀。一位朋友聽到我說我被帶走四天沒有睡覺,寬慰我說也還好,反正我本來也不太需要睡覺(因為我之前就有失眠問題)。我當時沒有告訴朋友,那不是我需不需要睡覺的問題。整整四天我沒有合過眼,一直坐在一張木凳子上,連上廁所的需求在一開始都是不被允許的。我面臨他們隨時的突擊審訊,他們試圖在我疲憊不堪時找出我陳述裡的邏輯漏洞並以此恐嚇我,要我出賣朋友。我在完全沒有睡眠的同時,還需要保持時刻的清醒與理智。我對著他們撒謊,並咬死了我沒撒謊。那是非常考驗心理素質的博弈,我坐在審訊桌的另一端,不被允許擁有任何隨身物品,看不到他們的電腦,不知道他們到底掌握了多少內容,我只能賭。我賭他們找不到證據,形成不了證據鏈,定不了我的罪。(當然,如果找到了我也得否認)
看到作者寫的「故土上的異鄉人」的感觸很深。我並不來自德黑蘭,我來自伊朗的伊斯法罕。這裡的方言是Lori語。每一次伊斯法罕的警察聽我報完我的身份編號後,便會略帶驚異地發現我是本地人。他們會用Lori語審我,威脅我,跟我套近乎。我從未搭過腔。我不願意在這些場景下使用Lori語對話,我無比厭惡並且痛恨這些本地警察使用方言審訊我,嘲笑我。他們笑我愚蠢,笑我放著這麼好的日子不過搞這些不值當。他們說會做這些事情的都是住在伊斯法罕的異鄉人。我內心厭惡並發笑,好啊,真好!異鄉人真好!沒有本地人的高高在上,精緻利己,還遠比本地人勇敢無畏!我永遠敬佩伊斯法罕的異鄉人。我非常自願加入他們。如果此地的警察要拿Lori語作為讓我加入背叛參與共謀的橄欖枝的話,我寧可放棄。我亦是我「故土的異鄉人」,我亦是「出走的娜拉」。
“WOMEN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用免于审查的中文书写当代史的初稿。欢迎您订阅我们,并帮助防火墙内的朋友邮件订阅我们;也欢迎您捐助和分享我们的文章。请联系[email protected],为报道提供线索或加入我们,成为撰稿人。我们会努力保证您的信息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