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被WeWork迷住了眼
航通社首发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航通社微信:lifeissohappy 微博:@航通社

书航 10月16日发于北京
这几天,我很困惑,为什么 WeWork 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遇到困难,以及被人否定。
国内的共享办公、创客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领域,比WeWork要早一年多经历生存危机,这也是因为它们相对更混乱和缺乏竞争力。
以前,民间或有政府扶持的各种“共享办公”在各大写字楼、高校及开发区纷纷挂牌。在此类创业浪潮最红火的时候,其它一些“卖水”的生意也纷纷涌现,如办公桌椅、绿植甚至宠物猫狗的交易。
中国的各种共享办公类服务,基本都可以归结为做“二房东”的,既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也没有知名度。遇到不景气,随着大量创业公司自身的倒闭,这些配套业务也会跟着收缩和消亡。
但WeWork总有一种能力,让人觉得它会成为那个例外。
此前我曾经想:在共享办公空间领域,如果别家做的不好,那可能还是它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连WeWork都不行了,那才能怪到整个行业身上。
实际情况跟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完全不同。The Verge、《华尔街日报》等很多报道综合起来,就是创始人亚当·诺伊曼一家子在努力维护一种画皮一样的表面光鲜。这家公司并不能用它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外表,和频频举办的鸡尾酒派对、万圣节之夜、内部观影等活动,来构建国内同行一直苦苦寻求而不得的“核心竞争力”。
但问题是,我们已经经历过Theranos——而放眼创投圈之外,更是有过让套中人羞愧难当的麦道夫庞氏骗局。要是WeWork果真如现在的报道所说有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以及其他很多人——却没有第一时间看出来呢?或者,我们可能看出来了,却没有坚定信念地唱衰呢?
很多报道都无法解答这个疑问,反而让我自己看起来,越来越像个无法发现“房间里的大象”的傻瓜。直到我开始看在IPO尝试之前写WeWork的文章为止。
打开2018年6月6日《连线》英国版的一篇稿子,那是一篇很标准的探营式文章,是按照“正面报道”的样子来写的,也是我们所有人当时看WeWork的那种感觉。
看的过程中,我既释然——自己不是最蠢的那一个,也恍然大悟——我们现在已经淡忘了WeWork带给过我们的感动,而正是这种感觉,让当年的人们毫不怀疑它虚高的估值,和现在看来空无一物的承诺。
就像恋爱中若是遇人不淑,你会痛恨自己当初为什么瞎了眼一样。如果你投入资金或兴趣到一家后来被剥得精光,露出“画皮”之下本色的初创公司,大概也会有类似的懊悔。
对WeWork来说,现在它所经历的“剥皮”过程,其实就是用传统的空置率、现金流、租约期限、回款等数据来评判WeWork的地产生意。这是强迫一个艺术特长生去考文化课——把它实际上最不擅长的地方,跟别人(它招股书提到的最大对手IWG)擅长的进行对比。
你还不能说这对它不公平,谁让它想要上市呢?一个人最丑的照片可能在ta的身份证上。一台手机最难看的样子要去工信部网站里找。而IPO就更是这样一场剥去所有衣服和卸下所有妆容的“公开处刑”现场。
你无法想象一家传统的地产企业,给办公室做了精装修之后就能变得跟WeWork一样吸引人(看看地产商们出品的Soho3Q和优客工场吧)。就好像每个说要复制硅谷(包含中关村)或再造香港的城市,最后都只能做回它们自己。
事实是,只有WeWork同时存在充满仙气的创始人,不讲究投资回报的政策,和不按套路出牌的运营法则时,再跟精装修和国际范儿的运营结合起来,才能维持这种现实扭曲立场。在中国,WeWork的外企身份就更是婆罗门一样金贵,其它国内创业者很难轻易企及。
也就是说,WeWork长期以来供给的并不是那些办公桌和会议室,它卖的是气氛、满足感和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参与感。
诺伊曼对《连线》表示,最初企业们来WeWork是为了短期租约,但现在它们开始为了这里的文化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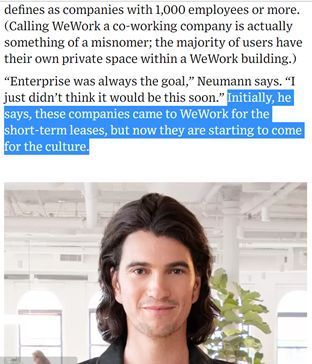
WeWork的模式是将大的办公室买下或租下以后分割成小单位,并佐以精装修和标准化的行政服务。这意味着其刚开始的客户来自个人或较小的企业,后续才有大公司派驻小团队进入乃至更大规模的入驻。
但较小的企业,比那些传统办公室租户(比如说很大的公司),到底应该付出更便宜还是更贵的租金才合适呢?
如果是像WeWork这种装修的话,那肯定是希望进行单价更高的出租。但它们初期反而是针对个人或小团队,打散了进行单独工位的出租。这就好像现在超市贩卖的小包装一样,虽然每单位售价更高,但包装的量小,总价还是负担得起的。
重点在于,WeWork的价值观还给了购买者一种名正言顺地付更贵价钱的理由,好像我们虽然没钱买奢侈品的包包,但买同一个牌子的口红总买得起一样。
是的,WeWork是科技范儿的奢侈品。一个WeWork工位跟星巴克和“共享自习室”相比,可能产品质量打平或甚至都不如(比如像咖啡馆一样吵闹;使用公共WiFi没有加密等等),但这是你进入奢侈品入门门槛的一只“口红”。
硅谷有很多这类玩意儿,像是Theranos(宣称用一滴血检验什么基因疾病),Juicero(普通铝箔包装的压缩果汁,假装必须用专用设备才能榨取),面糊一样的代餐,喝露水、蒸馏水或是喝油。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心诚则灵”的高技术信仰。
我曾经在 Apple Watch Edition 尝试进入奢侈品手表领域之初写过,硅谷新贵们想要重写游戏规则,砸烂旧世界的奢侈品厂牌,构建起新的,标榜热爱自然、简朴、热情、有好奇心(虽然实际往往并非如此)的生活方式。
WeWork先是试图说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二房东,此后又通过重组the We Company统一品牌,将贩卖生活方式的隐喻公开,并延伸到租房和办学校。我想老老实实卖办公室的IWG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玩,也不打算玩这个。
WeWork诞生的时期,不仅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百废待兴,大型办公室、写字楼出租难的时期,更是互联网创业即将开启大幕,导致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将从谷底回升的时期。所以,在那个时期之下它的商业模式是成立的。
而且,只有把WeWork跟普通的房地产公司放在一起比才能发现,当时新增的小需求大多来自互联网初创公司,它们都愿意往WeWork跑。
复苏时期,市场上的所有人确实都会增长,但增长幅度、受益幅度不同。在这些新增的份额当中,WeWork受益于其“生活方式”光环,而分走了更多的部分。
现在,当初新增的这些份额如海水退潮一般完全的退走了,依赖这种特定方式增长的WeWork自然首当其冲,原有的房地产企业至少可以守住原有的份额。(想象一下共享单车兴起时自行车生产厂家的不同选择。)
提出IPO之后,市场和媒体会非常严厉,但它们要求的其实并不是让所有公司都回归到朴实无华的乡土气质中,它们需要的只是你公司能持续盈利。
但WeWork(及其它行业中大量亏损运营的公司们)的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恰好是只有用大量烧钱才能创造的。它不合常理的快速开店也是必须的,不然它没那么进取,就难以拿到软银的融资。
甚至某种程度上讲,创始人大卫需要用龙舌兰酒和私人飞机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对外的吸引力,也都是必要的。似乎唯一值得指摘的只有过分的任人唯亲,把企业布置的就像个家族企业一样。让投资人以更大的怒火来批评他的生活作风。
我们还必须正视媒体起到的作用。
原本,《连线》们是抱着完全朝圣或好奇的心态,毫不怀疑地照单全收被营造出来的全部人设。电影《头号玩家》的前几分钟和《毒液》的开头都辛辣的讽刺了这种对科技创始人的盲从与崇拜。
现在,科技媒体(或财经媒体的科技报道组)开始尝试着对一切它们曾经崇拜过的事物祛魅还原,并沉迷于这种令曾经的崇拜对象心惊肉跳的,充满正义感的游戏当中。但科技媒体的前辈——政治及财经媒体,早已经历过一波从党争、扒粪、揭黑到建立“第四权”的跌宕起伏。现在,它们在劝告刚刚尝到甜头的科技媒体,在破坏的同时,要善于建设;要给出可行的方案,而不是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WeWork 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它已经失去了当初勉力维持的神圣光环,无法阻止人们后续用看其它地产公司的“狭隘”眼光来衡量它。所以此时它是否裁员或是否停止扩张,都意义不大。
当初是什么让WeWork重新粉刷过的办公室具备了灵性,成为众人趋之若鹜的朝圣地,我想现在我们不应该忘记。就像所托非人的少女,必须记得当初自己为什么会爱上这个坏家伙。否定这些也就同时否定了当初自己曾度过的时光,曾追求的目标和曾付出的真心。
那种感动和沉迷于时代进步中的感觉,在如今遭遇大环境寒冬或个人逆境的你我看来,是尤其值得回味的——人终有一死,而那可能的的确确是我们短暂一生中,极少数值得追求和铭记的时刻。
航通社增值会员服务“航通社的朋友们”火热开启订阅!请点击查看详情

寻求转载授权,请联系航通社助理(ID:hangtongshe)或发邮件给 [email protected]
